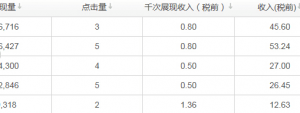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一个很小很小的林场。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户数大概80,人口不到300。
林场地处长白山老爷岭,群山环绕,居住区就在山谷中央。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我们林场四边都是好风景,东边是漂亮的山,南边是美丽的山,西边是雅致的山,北边是青秀的山。山都不高,最高的那座也只有998米,山顶上有一座五层砖石结构的瞭望塔,是父辈人拉肩扛运上去、修起来的。
小时候我总喜欢爬到塔顶看世界,然后感叹:“大海啊,都是水,没见过;森林啊,全是树,我种过……”我特别喜欢看一片青绿连绵不绝的样子,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也特别喜欢听风吹过森林沙沙的声响,糯糯软软,低语喃喃;那条通向外界唯一的山路,白如软玉,细若飘带,蜿蜿蜒蜒,兜兜转转,就是不知道她通向的远方,有没有我的梦想和期盼。
林场中间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河没有名字,发源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闲得无聊去找,只知道是天然的山泉水,很甜、很清澈。水里面也有鱼虾,很小,大致验证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语。水很浅,平缓处二、三十厘米,最深的地方也就是七、八十厘米。但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夏天在里面游泳,精力无限的男孩子,五六个就可以搬石头建成蓄水大坝,一米深、三米长的泳池,足够只会狗刨的我们在里面折腾。
秋天的时候,河水的拐弯处,深水区有很多漂亮的鱼,个头都不大,但是也可以用来炸酱,改善伙食。我经常干的事情就是用绳子拴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放一点馒头屑,插上油毡纸做的简易漏斗,扔到鱼聚集的地方,然后姜太公钓鱼,饿者进瓮。收获一般都有,但不会太丰盛。有一次我正在低头看有多少鱼进瓶子,突然脚一滑,直接掉进水里了,咚咚咚喝了几口水。迷茫之际,悲从中来,我心想:完了,吾命休矣。略一醒神,我发现原来水不深,站起来就完了。于是,午后深秋,杨柳河畔,落汤鸡般的我,在齐腰深的水中凌乱不堪。三十多年后,我想到这场景,记忆如昨。
到了冬天,小河就是天然的滑冰场,冰层厚度一般超过1米,冰刀、爬犁、陀螺……想玩什么都可以。孩子们成群结队,疯作一团,不分男女,追逐嬉戏。刺骨的寒风挡不住滑冰的热情,回家吃饭的呼喊,都叫不回玩疯了的小孩儿。冬天野外疯玩,有个秘诀:使劲折腾不能停,否则汗水结冰,冻得不行,容易生病。大年三十晚上,老娘一定会把我们哥俩儿赶去河里去冰上滚一滚,然后嘴里念叨:咕噜咕噜冰,越活越年轻,百病不生……

▲雪上滑冰
山里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数量不详。我记忆深刻的有:从屋檐下掉下来吓唬我的美杜莎、在菜园里扎到我脚丫子的小刺猬索尼克、不小心把自己的角挂在栅栏上被活捉的梅花鹿、偷鸡不成被爷爷杖毙的黄鼠狼、偷兔子不成但成功逃逸的花狸猫。野生的佩奇从来不见外,饿了就到菜地撒野;野鸡也是常客,经常被追得从低空飞过;熊大熊二比较悲催,偷玉米被抓个现行,被三支猎枪吓得屁滚尿流,逃窜速度那叫一个快,原来它们也可以是风一样的男子。

树林和小河里雪蛤很多,秋天的时候膘肥体壮。我七八岁的时候,爷爷经常在上午八九点钟,带着我和哥哥,装上馒头、捞网出门,下午两、三点钟我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带回三、五十只雪蛤。晚上六七点,拿雪蛤、大酱炖土豆,看得人口水直流,我们吃得汗流浃背。北方的吃货一般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句谚语,但未必明白真正的含义。这个龙不是Dragon,而是一种鸟,东北特产,叫飞龙。飞龙喜欢吃玉米,它有一个“好”习惯,吃一口,抬一次头。于是,聪明的我们就发明了挖斜斜的小洞,洞里放玉米,洞口下套子的专业捕获工具。小伙伴们常有收获,我多次尝试,却从未得手,心里比“好酒而不善饮的东坡”还要遗憾。邻居王小二经常“不经意”手提飞龙从我家门口经过,那洋洋自得的劲儿,好像昨天炖的大白鹅。

▲雪蛤、大酱炖土豆
山里的植被更是众多,白桦树的汁液很甜,生津止渴。用刀子在树身上掀起一块倒三角型的树皮,然后张开大嘴等着汁液掉进去;狗枣子(野生猕猴桃)拇指盖大小,放在被子里闷几天,香甜可口;高粱果(野生草莓)其貌不扬,但香气扑鼻,只需一个,满室飘香;榛子的壳硬硬的,用牙咬是不行的,要用石头敲;野核桃不能直接用手摘,外壳腐蚀性太强,粘在手上两个星期都洗不掉;山杏基本都不好吃,苦的太苦,酸的太酸,但是这都挡不住一个字——馋。野菜就更不用说了,婆婆丁、猴腿儿、猫眼菜、柳蒿芽、蕨菜、驴蹄子……春天来了,漫山遍野。采一筐,摘干净了,放在锅里用水焯一下,然后直接蘸大酱,那叫一个香。
蘑菇种类也不少,榛蘑、粘蘑、松伞蘑……最出名的是被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一曲带红的“俺们那嘎山上有榛蘑”,小鸡炖蘑菇特指的就是它。我最喜欢的是粘蘑,每年都是它从林地里先长出来,率先吹响蘑菇大丰收的号角,模范带头作用堪比春江水暖鸭。粘蘑炒辣椒,我的最爱。可惜的是,这种蘑菇太娇气,不能储存,离开老家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了。
林场的历史并不悠久,办公室和住房基本都是林业局在上世纪70年代沿着河两岸统一建的。住房大小一样,布局也差不多:两个卧室,一个厨房,房前有菜园,屋后有片山。在给林场的行政区划(如果有的话)命名上,林场人充分发挥了开放、诙谐、乐观、自信的精神,河的北岸叫“河北”,南岸叫“河南”,南岸有一块相对独立的区域叫“香港”。所以,大家的经常说的就是:“我住在香港,刚从河南回来。”听听,局气不?“河北”和“香港”住的是林场工人,上班拿工资的。“河南”住的是农民,靠种地和参与林场春种冬伐等工作谋生。虽说,工人和农民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在我印象中,没有出现过“河南”“河北”有什么大的冲突发生,可见老家民风之淳朴。
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大家基本上都是早睡早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开灯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败家行为。冬天的时候天黑的早,晚饭经常是摸黑吃。我一闹着要开灯,老娘就来个神句:“怎么着,还能吃进鼻子里去?”马上闷头吃饭,屏住呼吸。夏天的时候,白天很长,三点就蒙蒙亮。大学暑假回家,睡得正香,猛听得霹雳一声吼:“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懒觉!”睁眼一看太阳高高挂,阳光火辣辣。起身穿衣,洗漱完毕,一看呼机,才五点十一。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春天上山种树,冬天上山砍树,干的都是重体力,很是辛苦,也没有多少收入。印象中,冬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要早起做早饭、吃早饭、做中午要带的饭,然后穿上厚厚的棉衣,把一壶开水和饭盒放在一个放了很大鸡毛垫子的挎包里,骑上自行车上山。晚上天黑了母亲才能回来,进了家门,脱下湿透了的鞋子、棉衣,就又要开始做晚饭了,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我们兄弟两个都到县城上学,微薄的收入就不够支撑我们的学费了。母亲开始在木材车间车板子、后来也卖过水果、糖葫芦;父亲开过三轮车卖饮料、载客,也办过白酒厂,可惜没有成功。我和哥哥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离不开父母的节衣缩食、含辛茹苦。
哥哥高中毕业,考上了林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回到林场做了技术员,娶妻生子,在老家开枝散叶。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在嫂子的支持下,天资聪慧的他现在已经独当一面,成了林场业务的中流砥柱,也算是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侄女也马上大学毕业,开启新的旅程。未来的生活,想见就会很幸福。
而我自己,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二十多年,工作顺利,也算是成功地扎下了根。妻子贤惠、女儿贴心,该有的都有,衣食无忧。
父母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从林场搬进县城住到了楼里,屋里有地暖,不再需要自己劈柴、烧炕,少了很多辛苦。林场退休的福利还是不错的,父母的退休金每年都有一些盈余,经济上不再有压力,吃喝自由之余,每人也有了一件貂皮大衣。
林场由于风景秀丽,几年前被划成了国家自然保护区。林场的老居民全部迁出来住到了县里,林场单独在郊区盖了一个小区,还是熟人在一起,只是“河南”“河北”从隔河相望变成了楼上楼下。
疫情终于结束了,今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陪父母住了一个星期。闲暇之余,我让哥嫂带着我们全家回林场转了一圈。

▲儿时的家
林场已经荒无人烟,几年的风吹日晒,大部分房屋都已经破败了。我的出生地在“河北”林场入口大牌子下的第一间房子,她还挺立着,但我对她已不大有印象了,只隐约记得当年发大水我是从这里逃出来的。“香港”的家,基本承载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房前的李子树还在,是我当年从几公里外的山上移植过来的,可惜没有等到结果子我就上大学走了,不知道好不好吃。屋后的樱桃树也在,每年果子成熟都比邻居家晚一个星期,馋得我总是控制不住地去偷吃。山脚下的鱼池已经被填平了,那是我和哥哥用铁锹挖了一个月的成绩。门前的灯笼杆也倒掉了,每年过年我和哥哥都要去山上砍一根新的回来,越高越好,最差也要比邻居家的高一点点儿。
房子的门窗已经没有了,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没有熟悉的家具,但墙上的那抹绿油漆还有当年的印记。主房间是爸妈的,吃饭也在这里;小房间里住的是爷爷和我们两兄弟。爷爷很疼我,经常把哥哥支出去,偷偷给我好吃的。麻花、大列巴、山楂,啥好吃的都有,那时候在我眼里,爷爷就是现实版的哆啦A梦。走进小房间,迷蒙中,我突然看见了爷爷正盘腿坐在炕上摆弄鞭炮,冲着我说:“快出去试试响不响。”一瞬间,泪湿眼底。我慢慢走出来,静静地在房门口站了很久。眼前,荒草丛生、林木森森、皑皑白雪掩映着不尽的凄凉,凛冽的寒风伴着刺骨的冰冷。恍惚间,我仿佛又听到了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又看到了那个飞奔而回的自己。
女儿和老婆玩雪的打闹声把我拉回了真实的世界。赶快回到车里,打扫女儿鞋里的雪,她不知道怎么弄,可不要把她冻坏了。车子发动了,很暖和。回头望去,老房子渐渐远去,林场渐渐远去,记忆也渐渐远去。

▲玩雪的女儿
小时候,家很大很大,妈妈叫吃饭要十几分钟才能跑回来,气喘吁吁;
小时候,家乡很小很近,一口气就能跑遍林场的每个角落,追狗赶鸡;
现在,家很小很小,一百平米的房子拥拥挤挤,喘不过气;
现在,家乡很大很远,几年都走不回去,只是偶尔才能出现在我的梦里。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