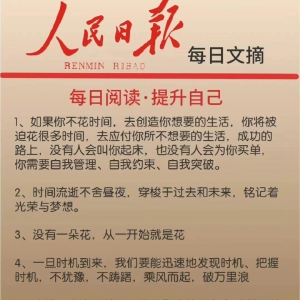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我这一生见过的河流太多太多了。它们有的狭长,有的宽阔;有的弯曲,有的平直;有的水流急促,有的则风平浪静。它们的名字,基本是我们命名的,比如得耳布尔河,敖鲁古雅河,比斯吹雅河,贝尔茨河以及伊敏河、塔里亚河等。而这些河流,大都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或者是支流中的支流。
如果说这条河流是掌心的话,那么它的支流就是展开的五指,它们伸向不同的方向,像一道又一道的闪电,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风,我都守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光明就在河流旁的岩石画上,在那一棵连着一棵的树木上,在花朵的露珠上,在希楞柱尖顶的星光上,在驯鹿的犄角上。
看来最不想丢的东西,却最容易撒手离去。
你爱什么,最后就得丢什么;你不爱的,反而能长远的跟着你。
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
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们逃走了。你们不要去找,想走的人是留不住的。
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光是一样的。你以为伸手抓住了,可仔细一看,手里是空的!
那晚没有月亮,星星也是那么的暗淡。人置身在那样的黑夜里,也就成了黑夜。
你让孤单的人和欢乐的人坐在一起,他们会觉得更加地孤单,还不如让他们单独待着,那样还有美好的回忆陪伴着他们。
她救活了别人的孩子,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
有人生,就有人死,就算是神也不能逆转。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
世界上没有哪一道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虽然愈合后在阴雨的日子还会感觉到痛。
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
我们无所顾忌地拥抱在一起,为这春光注入一股清风。那是最缠绵的一次亲昵,也是最长久的一次亲昵,我的身下是温热的碱土,上面是我爱的男人,而我爱的男人上面,就是蓝天。在那个动人的缠绵的过程中,我一直看着天上的云。有一片白云连绵在一起,由东向西飘荡着,看上去就像一条天河。而我的身下,也流淌着一条河流,那是女人身下独有的一条暗河,它只为所爱的男人涌流。
我和瓦罗加是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像鱼与水的融合,花朵与雨露的融合,清风与鸟语的融合,月亮与银河的融合。
我得感谢正午的阳光,它们把我脸上的忧伤、疲惫、温柔、坚忍的神色清楚地照映出来,正是这种复杂的神情打动了瓦罗加。他说一个女人有那么令人回味无穷的神色,一定是个心灵丰富、能和他共风雨的人。
男人的爱就是火焰,你要让你爱的姑娘永远不会感受到寒冷,让她快乐的生活在你温暖的怀抱中。
一个女人如果能为一个男人幸福地晕厥过去,她这一生就没白活。
一个好男人,是不会追问一个女人的去处的。
我也哭着,我的泪水小部分流向脸颊,大部分流向了心里。因为从眼里流出的是泪,而流向心底的则是血。
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的。
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