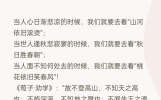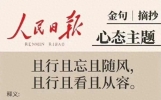我的故乡在孝感市孝南区三汊镇联欢村。我们子子孙孙要感谢先祖择居的审美取向,整个村的地势从东向西渐渐由高变低。绿树掩映下的村舍被六七口大水塘环抱着,村前的一条蜿蜒的小河从北向南缓缓流淌着,河上有一简朴的石桥。整齐的三四长排村舍被阡陌纵横的大片田野包裹着,田野上红的花,绿的草,晃动的人影,青蛙的长鸣,水牛的哞声等等是永恒的风景,这风景伴着袅袅的炊烟,如母亲一声声的呼唤就那么永久在留在记忆深处,让人温暖和怀念。
我最喜欢故乡的小河,她是我故乡的灵魂,她让那片土地灵秀沉稳端庄,极富母性。
春天,湾湾的小河象一条白色的纱幔蜿蜒在金黄的油菜花和绿翠翠的麦浪中,河水清澈见底,娟娟细流文静端庄如那片土地上秀美羞涩的少女;夏天,河水时而平静,时而湍急中裹卷着浪花,漫过河坝,淹没了小桥,倒灌进地势低矮的良田,那奔放热情的劲头,如祖祖辈辈朴实泼辣的少妇;秋天,水草枯黄,河床裸露,河水清浅。最冷时河道结着冰,冷峻又料峭。河道中碎石林立,每一个小小的鹅卵石都訢说着岁月的沧海桑田,它们每每会突然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凄苦的童年岁月。
一九六四年,我家老屋是一个土坯结构的房子,房顶盖黑瓦,墙体都是土砖垒起来的,当时的村舍每家基本上都一个样。堂屋两边的山架是用木桩做的屋梁和屋架,屋架间用杉木做的鼓皮镶嵌着,用桐油做过漆,很亮堂。我家房子共五间,叔叔家三人和我家六人住在一起。堂屋正东方,直直地立着一个庄严的神龛,神龛柱子和边檐上雕着漂亮的纹饰,纹饰如龙似凤。神龛中间,清晰地雕刻着“天地君亲师位”六个正楷字。神龛右边立着一个厚实的大粮仓,粮仓上雕着“丰衣足食”四字。堂屋中间放置着一个八仙桌。堂屋东边鼓皮正中用大木支架架放着一部家用水车。堂屋西北角,有一个半平方左右的木制鸡笼,鸡笼旁边是一个古朴的织布机。
一九六四的十月的一个夜晚,父亲同一个村民在八仙桌旁就着一盏煤油灯算帐,因为父亲是大队会计。母亲穿着大衣襟粗布格子棉袄,腆着大肚子在织布机上织布。父亲和村民都穿着厚厚的手工做的棉袄棉裤。亥时许,母亲突然腰涨难忍,她下了织布机,端着煤油灯慢吞吞进了卧房。她开始以为要小解,刚到围桶旁边,却感觉是孩子要出生了,她扶着床沿痛苦不堪地呻吟,铆足了劲喊了一声“我要生了!”。闻声父亲飞快地去找本村的接生婆,村民立马喊我同屋的婶娘。没等婶娘进母亲的房门,母亲往地上一蹲,肚中的孩子便血肉模糊地时蠕动到体外,在血泊中带着脐带乱蹬乱滚,生过四个孩子的母亲竟然害怕这个正蠕动着的小生命,看也不敢看,年轻的婶娘也不知所措,只知道扶着母亲。父亲同接生婆奔回了家。接生婆麻利地用嘴咬断了脐带,用手掏净了孩子口中的羊水,将孩子倒着一提,孩子就“哇哇”哭起来了。听着孩子在哭,父亲在堂屋外问“男孩还是女孩?”婶娘在房内一边回话:“酒坛子”,一边用母亲床边放着的片子将孩子身子擦了一遍后,将孩子用厚厚的小包裹布一包,放到了被子里。父亲一听“酒坛子”三字,一下子瘫坐在后门边的小凳子上,口中不住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母亲无力地躺到床上,无声地流泪。因为,这个孩子已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上面四个孩子中,三个女孩,只有老二是男丁。
婶娘和接生婆在卧房还没忙碌完,隔壁的大伯被叔叔喊来了。大伯穿着黑色的长马褂外套,拿着大烟斗,在寒夜中冻得真打哆嗦。他看着蜷缩在屋子内精神萎靡不振的父亲,在堂屋八仙桌边坐了良久。突然大伯大声而严肃地说:“二房里听着,把小鬼淹死它”。母亲一惊,大声哭起来,紧紧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父亲没有什么反映,实际上是默许了。大伯、父亲、叔叔就兄弟仨,这个大家庭的很多大事,都是由大伯决定的。婶娘和接生婆闻言到厨房提来了一大桶水。洗脚盆已倒满了水,放在了床边的搭板上。煤油灯下,灯光摇弋,脚盆里寒光闪闪。只要母亲心一狠,眼睛一闭,把刚出生的孩子脸朝下往脚盆里一放,一个小小的生命便会在几个亲人的眼皮底下被扼杀了。或者母亲将婴儿脸朝下,用大腿把婴儿的头压良久,婴儿也会一命呜呼了.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很多女婴就是这么残酷地夭折的。
此时的母亲突然停止了哭泣,朝着房外怒吼:“要淹死她,你来淹,我下不了手。我不做这样丧尽天良的事!”屋外的大伯一听,拿着烟斗站起来就走,摔了一句:“我是为你们一家人好!”接生婆连忙跑到父亲面前说:“二叔,一根草一颗露水。四个也是哺,五个也是养,饿不死她的,只不过每餐多加一把米。孩子投胎你家也是前世修的缘分。”哎!一条卑贱的小生命终于被她的父母接纳了。父母赐了她一个名字:多多。意思很明确,张家女儿太多了,祈祷送子娘娘下一胎送张家一个儿子!
人性的残忍自私,抑或是善良敦厚在关键时刻,往往无处可逃,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