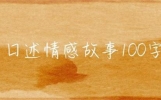《封锁》是张爱玲的一部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无奇,但却是她笔下最回味悠长的一篇。因为这篇小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缘。当时胡兰成无意间读到《封锁》,不禁为之惊艳,细细的读完一遍又一遍。一读倾心,再读倾情,之后他主动登门拜访张爱玲,成就了一段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
小说封锁讲述了一个平庸、琐碎而又充满可能性的短暂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旧上海封闭的电车里。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抽长又缩短,不断的不断的往前移。开电车的人紧紧盯住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一个有勇气的乞丐打破了寂静,他唱起歌来,开电车的司机百无聊赖跟着唱起来。电车里,公事房的人在暗暗议论同事;长相酷似的中年夫妻为熏鱼和裤子絮絮叨叨;脑袋酷似核桃的老头手里搓着两个油光水滑的核桃; 医科学生修改人体骨骼图被人围观;人们百无聊赖的或站或坐。
张爱玲不疾不徐的将故事场景娓娓道来,轻而易举让我们呼吸到当时的空气。封锁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着,如电车行进一般,单调,按部就班,被时间裹挟着不停向前。因为战争空袭警报,封锁了,旧上海陷入了寂静。时间和空间突然中断,人们赖以生存的秩序突然被打乱。空虚即刻袭来,各自找找事情,让目光能够暂时停留,才能不用去做思考,来填满这可怕的空虚。
电车与世隔绝,人群被时间一秒一秒压迫着。故事的男女主角,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擦肩而过绝不会看上对方一眼。然而因为封锁,她们在电车里,相遇了。男主角吕宗桢坐在角落,他是华茂银行的会计师,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他拿着妻子托他买的包子,轻轻揭开包装的报纸一角,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耐心的把印在包子上的反字逐个认了出来。他从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他是个老实的中年人,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甚至不苟言笑。他孤零零坐在角落里,一边吃包子,一边暗暗埋怨妻子对生活的过分计较、对他不够体贴。
吕宗桢的对面是一个老头子,右边坐着吴翠远,她是个年轻的未婚女子,二十出头,已经是大学里的英文助教。她整个人淡淡的,模棱两可地美着。家里鼓励她用功读书,翠远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尖儿上。然而家长渐渐对他失掉了兴趣,宁愿他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 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觉得,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人们顺从世俗规则,拼命的变得更好,而在翠远看来,真人就是可能打破世俗规范,跟随本心的自由人。
从吴翠远的长相、装扮和经历来看,她都是那种没有存在感的人,没人会注意到他的内心感受。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确定,他心里的怀疑与苦闷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就像在别人所说的只是一种无病呻吟,他只能靠给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打个A来宣泄内心的不满。
这时候,道路封锁了,电车停滞了,从前的生活里各种规则和束缚仿佛都消失了,这段时间充满了无穷新的可能性。刚好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使得生活突然朝着与日常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向发展了。
封锁使车厢的人都走开了,吕宗桢正好从容地吃他的包子,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他不想见得一个人,他太太姨表妹的儿子。为了避免和他搭话,吕宗桢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而后,又因为赌气般的要气他的太太,他对吴翠远调情,做给表侄看看,认准了表侄会打报告给他的太太去。
宗桢与翠远四目相接的那一瞬,充满了尴尬与误会,两个陌生人之间误打误撞地出现了交流的可能性。他们性格中那些早已压抑了太久的部分,忽然对一个陌生的异性放出光来。刚开始,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他碰巧瞧见她上车时候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 ”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翠远笑了,她觉得这个男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感到死灰般的内心里有一种东西被激活了,在那一瞬间被宗桢的真吸引住了。而宗桢对她的关注和问候也让她对自己感到满意,所以她突然觉得炽热和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对宗桢来说,从翠远的一惊一颦一笑中,他感受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女性风韵,他有了继续交流的渴望。这两个心思全然不同的人,在莫名其妙间产生了某种深层的交流,于是两个人惺惺相惜竟然在电车上谈起心来。她们谈到大学,谈到毕业,谈到工作,又谈到家庭。吕宗桢说:他对于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家里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他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翠远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

在街上一阵骚乱中,她们同时探出头张望,出其不意的,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这个时候,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人。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他跳出了自己正常的社会身份,回到了男人的本性。在封锁中,在这个与日常生活切断时间与空间的封闭空间里,没有责任,没有角色,他有幸还原为真实、自然、单纯的男人。而翠远长久以来渴望着的东西,恰恰是一个“真”字。
猝不及防的,“他们恋爱了。”翠远爱上了宗桢的坦诚,而宗桢爱上了翠远的理解和包容。这是两个人在生活中从来都没有过的一种感觉,纯粹而美好,却份外的不真实。
恋爱的女人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知道:男人彻底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所以,吕宗桢兀自说着,讲他银行的事情,家里的纷争闹腾,讲他的悲哀,甚至到他读书时代的理想。吕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宗桢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他准备重新结婚,却并未打算离婚,他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肩负着责任。
翠远甚至都想到,气气家里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活该气气他们也好。
这时候,封锁开放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如果他能够打电话过来,她一定会分外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然后,车上点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小说结尾吕宗桢重回到座位,是整个小说最震撼的一个点。在电车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两个缺爱的人遇见, 在短暂的相爱和互生好感后,又异常清醒的回归现实。好像是眯着眼睛做了一场美梦,梦境终究走不出现实。
现代人永远逃脱不开的,是社会中早已成型的规则和秩序,封锁中的电车是抽离现实社会的奇特空间,都市男女的道德困境,在封锁中才能看到。封锁开放了,世界恢复常态,男人回到自己原来好人的位置上去,宗桢做回他的好丈夫,好父亲,翠远做回她的好女儿,好老师,她们仍然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人们只是轻轻地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