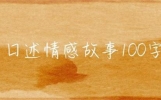作者:木木
谨将此文献给我崇拜的父亲和他心爱的五个女人
第三章:保姆成了爸爸的第五个女人
“爸爸,您定定地坐这儿等会儿,千万别走动,我去马路对面那家超市买点东西,好吗?”已经好几年了,我都是用对孩童的口吻同父亲说话。
“好的,你快点回来。”父亲看上去像个乖顺的娃娃。
我就势将出门时预备的小板凳放在路边的一棵杨树旁,搀扶着父亲坐了下来,便匆匆地向马路对面走去。
儿时,不小心把乒乓球压瘪了,父亲将瘪球放进热水里泡泡,居然神奇地还给我们一个圆鼓鼓的好球。收音机不响了,父亲只需捣鼓捣鼓,我们就又能听到小喇叭节目了。太阳落山,我们还会好奇地问,太阳要真是个大火球,为什么没把山烧了呢。而给我们答疑解惑的往往就是爸爸。上学后,解习题时为方法之笨拙步骤之繁缛犯愁苦恼时,每每经父亲那么一点拨,我们便会发现原来还有着多么简便快捷的解决途径。在我们幼小的眼里呀,父亲简直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二十来岁,涉世之初,颇有几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觉得父亲陈腐不开窍,总以为自己处处比父亲高明,不会象父亲那样一生平庸,一定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挫,棱角磨平了,头脑也清醒了。而立之年,突然明白,如果当初能多听听父亲的意见,该少走多少弯路,该有多少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
父亲的内心世界有着多么丰富深厚的宝藏啊!然而岁月无情,癌症夺去了继母、也是养育我长大的妈妈并未衰老的生命。脑血栓的一次次复发,严重地损害父亲的健康和智力。父亲还不到七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性情烦躁胆怯,渐渐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我做事时,父亲总要凑过来,或是孩童般的那么一种神态,好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或是一副焦急难耐的样子,似乎觉得我做事的方法不甚妥当,想指教又说不出个所以然。逢我有事要出门,父亲那种期待巴望的眼神,由不得人不备个小板凳搀着他一块出去。儿时,我一生病便彻夜哭闹不肯入眠,父亲就彻夜抱着我抚慰我,那时父亲温暖的怀抱是我最安全最有力的保护。而如今无情岁月,已使我和父亲彼此之间的角色发生了彻底的调换。父亲已变得那样稚弱,只能牵着儿女的衣襟过余生了。
“爸爸,我买了您爱吃的核桃仁,咱回家吃去,好吗?”我以最快的速度买了该买的东西。
父亲只随口应了一声,似乎并没在意我买回的东西,眼睛仍盯着不远处的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专心地看摊主补一个轮胎。天不早了,又吹着冷风,初春的天说变就变,父亲的抵抗力又弱,一旦感冒很容易使脑血栓复发,得回去了。
“爸爸,咱回家去,这儿太冷。回家看我择菜做饭去,比修车子的还有看头,对吗?”父亲倒还不执拗,任由我搀起了他,悄无声息地跟着我往回走,还时不时地回过头瞅瞅那个修车子的。
“爸爸,您怎么不大和人交谈呢?您开朗些,病便会好的快些。"
“你们上班去,老把我一个人关家里。”父亲像个受了憋屈的孩子。
“爸爸,那么咱给您张罗着找个保姆,家里能整天有个人陪着您,好吗?" 我终于说出了考虑已久的想法。“谁可愿意伺候我呀?”父亲无力地反问着。
这还着实叫我犯难。父亲年已古稀,脑血栓后遗症又常常使他连自己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找一个长期的保姆又谈何容易呢?不论怎样还是要试一试的,于是我拜托各位亲朋好友为父亲找保姆,并开出了不低的工资,还许诺节假日可以休息。父亲的房子地处本省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家里终日有个人,常常搀父亲出去街心公园、商场逛逛看看热闹挺好的。父亲这一生太不易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五十多岁时,我的继母又去世了。他既当爸又当妈地将我们姐弟三人抚养成人,如今我们都已成家,弟弟、妹妹又在外地工作,我尽量得想法安排好父亲的晚年。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老家甘肃的一位堂婶有个妹妹,四十六、七岁,身板硬朗,出身于穷乡僻壤,愿意做父亲的保姆。据说堂婶的这位妹妹,自小由于家贫又是个女孩,一天书也没念过,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十六岁时由父母包办嫁给附近庄上一户殷实人家的独生儿子。从一结婚就不讨婆婆的喜欢,丈夫还是个不务正业赌博成性的二流子。还因为生了两个女儿,常遭丈夫毒打,最终被婆家赶出了家门。两年后与县城里的一个下岗工人同居,当牛做马两年后,又被赶走了。由于两次嫁人的失败,她在那个小县城人尽皆知,处境更加不利。听说我们想给父亲找个保姆,又因为是远亲,早年她也见过父亲,就以出乎我们和所有亲友意料的爽快,夹着个包裹来到了我家,做了父亲的保姆。虽然她比我只大十多岁,可她既是堂婶的妹妹,我就称呼她蔡姨。
也就是蔡姨来我家个把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我去看父亲。父亲和蔡姨也刚起床,我却意外地发现蔡姨的枕头被子一并都被挪到父亲床上了,显然他们睡一起了。我正惊谔,蔡姨倒很平淡地对我说,父亲非要娶她,她也同意了,并且他们把结婚证都领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事先都不告诉我们做子女的一声呢?但转念一想,只要父亲晚年过得好些,我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再说嫁给父亲,就意味着得终日服侍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想必蔡姨也是权衡了利弊才做了决定的,就这样蔡姨由保姆变成了我们的继母。其实她和父亲所谓“婚姻”的实质,我和所有的亲友心里都明镜似的,只是没必要非得往明说。也许是继母仅大我十多岁的缘故,也许是她与我知识分子的母亲言行举止相去甚远的缘故,我总难开口叫她“妈妈”或“新妈”什么的,也无意细问她叫什么名字,仍称呼她“蔡姨”。
蔡姨除了身材矮小外,细看五官似乎也没什么异常,可就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错,从长相到步姿,乃至操着一口家乡土语中偶尔夹杂的一两句走了调的普通话,给人感觉无一不是令人难受的造作和不顺眼,实在是找不出美的地方。我和妹妹曾试图通过衣饰为蔡姨遮遮丑,却发现无论什么衣服穿到蔡姨身上,便会失去原本的丽质。有一次,我约一位学广告设计专业,深谙修饰打扮之道的朋友来家里,想让她顺便帮我参谋着买几套衣服改变一下蔡姨的形象,谁知那位朋友却硬是推托有事没答应我的要求。事后那位朋友向我解释说:“你若定要我改变你蔡姨的形象,那可真是给我出了大大的难题,我可实在没那逆天的本事。美就是和谐,倘若你蔡姨人走到大街上,便会成为整个城市不和谐的一个点,影响市容。”
蔡姨貌丑,却又偏偏爱俏,常常近于苛刻地挑剔我给她买的衣服针脚不细样子不合体,还会感慨道:“真是老了!年轻时家里(前夫家)是庄子上光景最好的人家,爱梅(蔡姨大女儿的名字)她爷当队长,每年都要给我们婆媳俩扯几身时兴衣服。有一年穿了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衣,惹得庄前庄后的后生们都围着我眼睛溜溜地转,害得爱梅她爸不放心,总打我。大姑娘小媳妇们全都眼红我漂亮,妇女队长要不是害怕爱梅她爷,不知给我找多少碴呢。现在穿啥都不好看了。”
我不禁感到惊诧和悲哀,她居然对于自己没有丝毫正确的认识。蔡姨先前嫁过去的那个山庄,儿时我随曾祖母走亲戚曾去过的。四周连绵的秃山、荒凉的土地,山民们把全部的能量都用于奔波生存活命了。饥饿的威胁、衣不遮体、精神生活的荒芜,早已使蔡姨老家的山民们对于美的审视麻木了。偶尔哪个“富裕”之家的年轻女人穿出那么一件鲜亮的衣服,山民们终年和黄土地一样灰暗的视野便会为之一亮,并令他们兴奋不已,由衷地惊喜道,看那边走过来的女子多好看!倘若城里的任何一位时髦女郎从山村经过时,那里袒胸露乳、蓬头垢面坐在房前屋后奶孩子的妇女,便会喊出全村人齐刷刷地从家里跑出来,象看天外来客般好奇,啧啧感叹道,这是哪儿来的人简直像天仙一般。其实他们所谓的“漂亮”仅仅是针对衣服而已。但那个闭塞的山村,据我所知,民风还是相当淳朴的,况且温饱还自顾不瑕呢,谁又有闲情逸致去挑一个“漂亮”女人的刺呢?大家总挑她的刺,是不是蔡姨在为人处事上颇不讨人喜欢呢?由于挑剔的厉害,从此我们姊妹替蔡姨添衣物便带上她,由自己去选购,可往往不论式样是否合身,唯价钱高便是她所爱。买了衣服又总是不穿,一律压了箱底,平日只找些我和妹妹弃之不穿的旧衣服随便往身上一凑合,也不再那些挑剔那些衣服有多么不合体,甚至连穿她身上滑稽可笑都不顾了。在老家亲戚来家做客时,蔡姨却将来我家后购置的新衣拿出来,一天一身新地换着穿,没来得及上身的还要抖出来给老家人显摆,还赤裸裸地对人家说,我总归是嫁去老头的人。
不论怎么说,蔡姨服侍父亲还是颇尽心颇温顺的。一日三餐尽量按父亲的口味调剂,早晚搀扶着父亲散步,清洗父亲的屎尿内裤从不皱眉犯愁,逢父亲便秘时毫不犹豫地将手指伸进父亲的肛门抠出粪便。特别是父亲由于脑血栓导致的精神障碍发作时,则彻夜兴奋不眠,甚至发脾气骂蔡姨。蔡姨总是彻夜相伴、不恼不烦,在父亲面前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这些着实的感动了我们姊妹,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老伴,父亲晚年不再寂寞,心情也似乎开朗了许多,让我感到了蔡姨在我们家的重要性。于是便从心里接纳了她,主动和她亲近,以致后来父亲让我把他的房产证、存款和工资一并交于蔡姨,我也照办了。
渐渐地蔡姨也不再象初来时那么拘谨了,做事放开了手脚,说话也一改低眉顺眼的模样,这时又令我生出许多颇为不顺眼和不舒服的感觉来。诸如蔡姨吃过饭后舔盘子舔碗的举动,去商场超市买食品时非要乘售货员不注意偷着先品偿一口不可的习惯,与亲友礼尚往来现时出的抠抠缩缩的小气。家中所来之客,无非是父亲的旧知故交,若不是挂念父亲,谁闲来无事肯屡屡登门?可蔡姨见客人来,从来都像是事不关己似的视而不见,躲一边不问客人更谈不上招呼客人。偶尔有位客人经不住父亲的一再挽留陪父亲吃顿便饭的,蔡姨还象平常一样,怕饭菜剩,做得紧巴巴的刚勉强够吃。而蔡姨自己总是钻躲在厨房不闪面的,等客人走了剩多少吃多少。有时碰上热心的客人,千呼万唤始出来,蔡姨坐到餐桌边不吃,却定定地看着客人吃。客人问她为什么不吃,她却做作地说:“我饱着呢,你们吃就行了。”几次竟弄得人家客人不好意思吃了。我发现后提醒她,以后再不要死盯着看人家客人吃饭了,不礼貌的。从此再陪客人吃饭时,竟又发现蔡姨极不自然地低着头,那双过大而又无神的眼睛完全不知该往哪儿瞅似的。
蔡姨还真会“撒娇”,当着父亲子女孙子的面,居然好意思嗲声嗲气地称父亲为“黄大哥”,看电视时公然将头枕在父亲腿上。有时父亲放个响屁,她就手伸到父亲的屁股后掬一把“臭气”到父亲鼻孔前说,给你闻闻多香,实在是让人看着不入眼!可不管咋样,父亲总是有人照管了,我也有自己的小家庭,没事少回几次娘家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