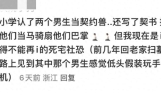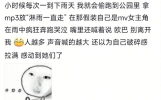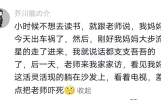2018-05-26 07:12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沈家农民
早年,哪家孩子不是贼
乡野孩子总是“折乐”的(衢州话,意即顽皮),用当下的话说大多都是熊孩子。于今想起,或者说时常回味的还是少时的一些偷偷摸摸的苟且。

不知道具体几岁,只记得那是炎热的下午,生产队中途歇工。许多人东倒西歪懒洋洋躺树阴、屋檐下,似睡非睡。突然,队长咬着烟筒,流着口水,含糊不清地嚷嚷着,四处找烟筒。一个个被他踢醒却默不作声相互看看,就是不告诉他烟筒在嘴上,任由他着急上火……
就趁着这混乱。我悄悄潜入屋内,直奔碗柜(也称菜櫥),直取最下层角落那团纸包。那层纸油油的,剥开是块肥肉样的东西,有股很特殊的气味。心想这块肥肉肯定珍稀,否则不会藏这么好。不及细想,一边猛咬下一大口,一边包好塞回櫥角。然后,若无其事转到屋后,没见有人。就急速嚼。还没品出啥滋味,便囫囵吞下肚里。

再走回前门,坐于树阴,正待回味。那屋的女主人就大呼小叫起来:怪了怪了,刚刚放菜櫥的香皂,怎么就被谁掰去一块了!还是用牙咬的!
香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肉。悄悄离开人群,躲得远远的。不一会,肚子便咕噜咕噜的来劲了……

这真的并非勇于自我揭丑,实际上早年乡野孩子类似的“偷吃”,比比皆是,几乎个个都是“惯偷”。但凡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以备待客不时之需),大人必定是要挖空心思东藏西匿的,明里防猫避鼠,暗里却是严防死守这些“讨债鬼”。一经被其看见过,那想不被惦记是不可能的。大人一出工,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结果啥也没找到,那就恨恨地拿过灶台上的酱油瓶,猛喝几口,咂咂嘴,味道也不错。心想那有啥好吃的,最多与这酱油差不多吧,于是心里方有渐渐平衡。

不仅如此,小伙伴们还隔三差五相约,互为引“贼”入室,里应外合,到各家搜寻一通。这也颇似长大后朋友间的轮流做东,相互请客。倘若哪家搜出深藏的“兰花根”(油枣)、橘饼之类的珍馐,那个“做东”的孩子尽管自己没抢到一星半点儿,但仍然格外的神气活现。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便在伙伴里具有了绝对的“领导权”,及至在另一家的喜出望外。倘若哪家毫无稀奇的,一群人便围着一坛腌菜、腌辣椒什么的,大快朵颐。“做东”孩子便拼命吃,以示他家的腌辣椒胜过兰花根,也显示他不怕辣的勇敢……
对此大人虽然心知肚明,可也不好发作。一则捉贼捉脏,二则法不责众。何况“祸”起萧墙。恼归恼,气归气,只得以后再倍加小心防范。于是,所有需要珍藏的东西,比如豆种、玉米种等等,统统高高地悬挂房梁。而对于梁上之物,我们再怎么馋,也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后来读书读到“梁上君子”喻为窃贼,那很“理解”的,梁上的物什也要偷的,那真是贼了。

说也奇怪,早年乡亲对于孩子们的偷吃,却是非常宽容,并不视之为“不良”而打骂谴责。如果哪家吃的被谁孩子偷了,再大呼小叫的骂街,大多会被邻里非议。相反倒有点“私藏”美食,却被人发现的理亏。有的就索性用手巾什么包点,送于那偷吃孩子的家,让孩子解解馋,并声言解释本就早要拿过来的……相比之下,孩子讨吃,却是要被讥笑而看不起的。父母们无不谆谆教导孩子:嘴馋不能向人伸手。

孩提时期的我们,说也是的,整天就琢磨着吃的,到处转悠着找吃的。麻雀烤了吃,老鼠也烤了,野蜂窝烧了,蚂蚁窝也烧。至于广阔天地里的瓜果,更是不在话下。几乎每天都要到村里仅有的几棵桃树、梨树下转转,仰头数一数长出了几颗。只是豆米大,孩子们就号上了,那几颗是狗儿的,那几颗是麻雀的……梦里常见自己的那几颗红彤彤的诱人,醒来口水一脸,赶紧跑到树下,却是夜来风雨声,果落知多少。有时实在熬不住,毛桃就毛桃,摘一个衣裤上擦擦,有些涩有些酸,但也能饱一会儿。然而夜里就打摆子了(俗称“打半工”)。大人便数落:讲过多少次了,毛桃吃了要打摆子,就是不听。一边就脖子、鼻梁、后脊背的拧一通——长大后知道这是刮痧,那时乡里人却是包治百病的,感冒拧几下,中暑拧几下,积食拧几下,头痛拧几下,脚痛也拧几下。小孩犯错也拧几下,不过这回拧的是耳朵或胳膊腿。
好不容易盼到桃子发白梨子发青,可恨那人家的老太婆越发看管得紧了。整天拿根长长的竹竿,俨然佘太君出征,誓死保卫河山。她也只是驱赶,宛如赶一群麻雀。其实哪是我们的对手。瞅准老太婆回屋小解啥的,我们就蜂拥而上。当然不用攀树,树小就合力摇晃,树粗就冲过去用身子撞击。如此,那果子就噼里啪啦落一地。老太婆尽管装着回屋,一个回马枪,无奈果子落地了。我们就理直气壮的说:还不兴捡么?地上的一定是你家树上的么?老太婆就带着哭腔的骂——你们这些天收的,再等几天不行啊……这情形就很是唐朝诗人杜甫所记了: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梨”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偷吃,这简直就是孩子们的一个游戏,既解馋果腹,又有“智取威虎山”的刺激,乐此不疲。

秋天是美丽的,美在有着丰富的果实。山上的山楂红了,野猕猴桃熟了,毛栗爆了……这些都不用偷,尽管尽情采摘。即使田塍沟渠边,有一种荆棘长着荸荠大小的果子,等黄了红了,洗净刮掉皮上的毛,再用竹片捅刮掉内心的籽核,酸酸甜甜,甚是好吃。不过这些野果吃多了,挖肚子。此时自然就想起某某山脚下,某家的番薯地。山里人家可谓遍地番薯,但是那时有一种我们叫“五十公”的番薯,皮特别红,内里却是晶莹剔透的白,那味道远超雪梨。因其不出淀粉,一般生吃或早餐混稀饭,所以只有极少数人家在隐蔽处(旮旯里,或普通番薯丛中)种点。尽管种的时候遮遮掩掩,其实早就被孩子们惦记着了。
再怎么隐蔽,我们还是可以一眼认出。因为其叶子与普通番薯叶不同,呈多角状,且其藤青里泛白,藤节有些微红。这活儿我们称之“撬地雷”。我们倒真是有意的“瓜田李下”了。装着内急,老远夸张地提着裤子,奔至“雷区”,拉下裤子蹲下,然后拨开藤蔓,用备好的竹片,从容不迫地掏。这个“五十公”特浅,其实捏着藤根部,一拔就拎起一窝。但我们就喜欢那么慢慢掏,掏起一只,袖子上擦擦就吃。再掏再吃,突然果真内急,那就不妨一边出一边进。然而,也是突然,不知道从那儿悄无声息跑来一群狗,在屁股下呜呜地,冷不丁还舔下屁股,未几,群狗为了争食就打起来了。不得不提了裤子,悻悻然走开……

当然,我们也仅限于此类的偷吃。生产队里的玉米、甘蔗、豆子等等,长得再好再诱人,尽管在那个饥荒的年月,我们都秋毫无犯。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那时农家自古吃食不分家,人家的总归是个人情,吃的东西总归是人吃。而生产队是大家的,是公家,公家就不存在私情,偷吃公家,就是破坏。轻者罚放电影,重者游街批斗。
及至现在回乡,乡亲们闲聊还会逗趣当年的偷吃等糗事。末了,免不了一声叹息——那时的孩子咋嘴那么馋、肚那么饿啊?!是的,我们曾经都是熊孩子。乡亲当年都明了,岁月也记着。早年糗事,偷得一份乡情,不知何处安放。
图片均由市摄影家协会王洁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