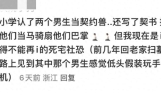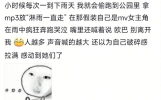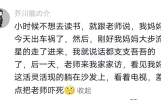我出生在1968年苏北的农村,苏北在江苏省范围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很苦,但再苦再穷,我们这些小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玩,是孩子们的天性。那个年代虽穷,但小孩子们很快乐,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书包一放下就跑出去“疯”,天天如此,在贫困的岁月里,象野草一样,无拘无束地生长着。
小时候,我和村子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同长大,干了不少让大人们烦心讨厌的糗事。
当然,有些事做的太过份,不仅闯了祸,也常受到父母的责罚,但父母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实在无效,屡教不改,父母也用鞋底或棍棒吓唬过我,但总是屡教屡犯,弄得父母也没辙!
1.捅马蜂窝
我家院子门前有一大片地,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宅基地的空地,我母亲辛苦打理成菜地,年年在上面种上茄子辣椒等,但就是不丰收,结出的果实小而弱,有的秧苗早早枯死。
原因是周围树太多,不仅根系吸走了小菜地的营养,而且遮住了阳光,菜地里的菜总长不好。
记得菜地东角有一棵合抱粗的槐树,树干高大,枝叶婆娑,据说是我当时去世已多年的爷爷小时候栽的,这么多年了,难怪长得这么粗。
这个树树干很粗,但可惜成不了大材,原因是树干不知是生虫子,还是自然生病,好好的一棵树,树干中部是空心的,我父亲经常仰望着这棵槐树叹息,说白瞎长了这么大,伐倒也没用,只能当柴火烧。
但就是舍不得伐倒,只因每年开春,这棵槐树开的满树一串串、肥肥嘟嘟雪白的槐花,香飘半个村子。
那个年代,槐花可是好东西,又好吃又能抵口粮的不足,所以一直让它长在那里。
让人心烦的是,树干中部是空心的,蚂蜂年年在里面做窝,而且这种蚂蜂的品种特别吓人,全身黑黄色,个头很大,身子很长,屁股下面略带弯曲的蜂钩很尖很毒,翅膀像直升机螺旋桨的叶片,飞起来老远能听到嗡嗡的,声音怪吓人的。
邻居家七十多岁的二大爷说,千万不要去招惹这棵粗大的槐树内的蚂蜂窝,这种野蚂蜂毒性可大着呢!有的人说的更玄乎,说如果被这种毒蜂蜇上,十几只的毒量可以毒死一头牛。
我们那时七八岁刚上一年级的毛孩子,从没被蚂蜂蛰过,没吃过被蛰的苦头,当然不相信老人说的话,依旧调皮捣蛋,找个法儿取乐。
住在我家屋后的邻居二毛哥,比我大一岁多,他天天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家前园后胡跑瞎拉,追狗撵鸡,非常调皮。
一天下午放学后,天气异常闷热,他带着我们六七个小孩子,原打算到门前马路对面大塘池去洗澡玩的,恰巧又路过菜园边这棵大槐树。
“机灵鬼”叫团结的小孩,发现树洞边进进出出的蚂蜂,就大声叫喊,让大家过去看。
二毛看到后出点子说,这树洞内肯定有蚂蜂窝,就带着我们去池塘边,每人用手挖一大团稀泥,去堵这棵槐树中间蚂蜂洞口,说是要把蚂蜂全封堵在洞内,困死这些蚂蜂。
在二毛的带领下,我们每人从池塘边挖了一大块稀泥,站着离树一两米远,对着树洞缝隙,狠狠地把泥巴砸了上去。
其他几个小伙伴砸完都跑得很利索,我自己家的大树,早听大人们说过,这窝蚂蜂不好惹,但又怕二毛他们嘲笑我胆小,所以硬着头皮最后一个上去用泥巴去砸。
没想到,蜂巢外飞回来的蚂蜂,发现洞口被稀泥堵住,洞内的蚂蜂也反应过来,纷纷从没堵住的洞缝中钻出来,里应外合,气势汹汹地飞过来攻击我们。
不幸的是,只有我跑得晚,被一只蚂蜂蜇到了额头。
这可不得了了!痛得我当场满地打滚,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家二哥听到哭声从院子里跑出来,弄清情况后,不仅不安慰,反而大声呵斥我太调皮。
那时农村条件差,根本没有打算把我送大队卫生所去医治的念头,况且卫生所缺医少药的,平时最多看个伤风感冒的,对蜂蛰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母亲赶紧用肥皂水往我头上擦,说是消毒,又去求外姓的邻家四婶子,说是女人的奶水可以治蜂毒。
但怎么折腾,我脸和脖子都肿得吓人,特别是两个眼睛肿得只有一条缝,什么也看不清。
丑不说,还疼痛难忍,浑身发烧,急得我用井里的凉水往头上浇,两个多星期都没去学校上学,天天躺在院子里的凉席子上熬着,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那个年代,农村各家孩子多,家庭贫穷,命贱像根草,大人们都天天忙着下地干农活,哪有时间和心思管我?
我那时想,可能我活不了多久,因为邻家二大爷和四奶奶都说过,这种毒蜂牛都能被蛰死。
还好,几周后,蜂毒慢慢被我身体吸收消化了,算是捡了条命,当时如果是一群毒蜂蛰到了我,唯怕就很危险了。直到现在,我见到蜜蜂都害怕,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2.炮仗插在牛粪上炸
那时,我们生产队大集体开了一个弹棉花作坊,专门加工棉花网套搞点副业。
弹棉花的机器安装在一间大房子里,紧靠机器的房子外面,又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房子,安装了齿轮和转盘,需开动机器弹棉花时,用两头毛驴转着圈子拉动转盘,通过齿轮传送动力,带动另一个房子里弹花机工作。
中午或晚上,六十多岁的生产队保管员张庆财就住在院子里面弹花机的房子里,边休息边看管机器。
每当保管员老汉张庆财要休息,我们几个调皮孩子,就悄悄溜到转盘房子,把转盘轰轰隆隆推动起来,带动另一个房子内的弹花机,声音特别大,把保管员张庆财吵醒后,气得他从床上爬起来,绕过大门边追边骂。
有一次做得更绝,春节时,有些小伙伴从家里买的准备年三十放的整挂鞭炮上,偷取下几个散炮竹藏在口袋里。
生产队养了许多牛,我们从院子里的牛槽下弄了一大坨牛屎,悄悄放在保管员张庆财睡的弹花机房门口,上面插上2个很粗的炮仗,一个小伙伴在旁边偷偷看着,观察屋里的动静,准备点火,其余几个小孩就跑去外屋推弹花机的大转盘。
当弹花机轰轰隆隆转起来后,就听到了保管员张庆财骂骂咧咧起床,准备出来追赶我们。
快出房门时,那小孩迅速用火柴点燃了炮仗,正当保管员气呼呼刚跨出门槛时,恰好炮仗响了,牛粪被炸得到处都是,蹦得保管员张庆财老汉满脸满身都是牛粪。
保管员气得当场跑去找生产队长告状,他早就知道是哪几个调皮孩子干的坏事,我们几个小孩都被家长好好教训了一顿。
3.歪脖子树上拉屎
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南湖地稻田边有一条很长的河沟,直通白马河,平时就是靠白马河的水,通过这条河沟为这几百亩的稻田灌溉浇水。
河沟两岸生长着许多大柳树和槐树,我们经常爬到大柳树上去玩,或者从大柳树上折新鲜的柳树技,扔下来喂给羊吃。
其中河沟边有一棵很粗的歪脖子柳树,也不知那个大集体年代的人哪年种下的。
由于这棵柳树又高又大,生长在河沿,年代久了,河沿泥土松散,长着长着就歪倒向河里,但没有完全倒下去,倾斜着身子顽强生长,树的脖子弯曲,小孩子们都它叫歪脖子树。
每年夏天一放学或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孩都会到河沿放羊或割猪草。歪脖子树倾斜着身子,我们很容易爬到树上去玩。
有年夏天,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在这棵歪脖子树所在的大河沟边的稻田里插秧,我们平时玩得好的五六个小孩,跟着大人到稻田边玩耍,都爬到了这棵歪脖子树上去玩。
有个叫团结的小孩真会恶作剧,他竞竟然先下到树杆的一半,倒撅着屁股在树杆上拉了一坨稀屎,屎和尿混合着把歪脖子树中间一大截弄得全是屎尿,他顺着树杆下半截跳了下来,在树下等着,看我们困在树上的人怎么下来,他在下面等着看笑话。
我们一看树杆上有屎尿,都不敢下去,不仅又臭又骚,关键是我们如果两手抱着树下,手和脚都得沾上屎尿,急得我们哭得哭、喊得喊。
树上有两个大一点的小孩,也真有胆量,干脆裤子也不脱,直接从树上跳到树下的河沟里。
河沟里常年都有水,只是对小孩子来讲,跳下去落差有点大,小一点的孩子从树上往沟里看都害怕,大一点的孩子跳下去也破水呛得够呛!幸好我们这些小孩很小时都会游泳。
其余小孩只有急得在树上大哭,边哭边喊在水里插秧的父母,父母这才赶过来,用铁锹和盆等端水,把树杆冲洗干净,上去把其余小孩“解救”下来,那调皮捣蛋的团结,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4.“拉帮结派”打群架
当年,我们生产队人口很多,村子也很大,村西头到村东头大约一公里多。那是个农村人认为“多子多福”的年代,平均家庭都有五六个、甚至六七个小孩,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在这样的条件下,村子里自然小孩子很多。一到晚上,院子门前、打麦场上、路边,到处都是吵吵闹闹玩耍的小孩子。
在一起玩的孩子多,时间长了,自然会产生矛盾,进而会分成团团伙伙。村子的东西头各为一伙,有时两伙还相互渗透,到另一头玩的,但会被本伙的人定性为“叛变”或“叛徒”。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公社电影队到农村放的电影都是政治性非常强的所谓“红色经典”电影,里面的人物中,塑造的所谓“好人”,都是一本正经的高大上,怒目圆睁,看谁都不顺眼,时时刻刻要给自己树假想的敌人,今天斗这个人,明天斗那个人,似乎世界上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只有他自己是好人。
这种洗脑的电影小孩子们看多了,自然都会去学。
我们生产队村东头,有个小混混叫张卫东,五短身材,长得很结实,打起架来真是虎!我们自然都怕他,平时都听他指挥。
他自封司令,带领我们十多个小孩,从军长到排长,每人都给封个官。他天天晚上召集我们在一起,每人拿着一根木棍,杠在肩上当枪使,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块和碎砖头。
在张卫民的带领下,一帮人吵吵嚷嚷,天天晚上窜到村西头,和同样自封为司令的叫王建国的调皮头子打群架。
双方一见面,都喊:“敌人来了,快给我冲上去,消灭他们!”,接着石头砖块,像雨点般砸向对方。
刚才还都非常嚣张的双方小毛孩子,黑暗中,见对方黑压压的一片,好像人多势众,马上怂得把小石头和碎砖头扔出去,便吓得如鸟兽散地跑回来,躲的躲、藏的藏,怕对方报复打过来。
加上看热闹的小孩,双方卷进去打群架的人很多,有许多小孩子头被砖头石块打肿打破了,有的小孩头上还流了血。
这可不得了了,双方受伤小孩的家长便会带着受伤的孩子,去找带头闹事的两个司令张卫民和王建国的家长,最后也是陪几个鸡蛋补补身子了事,没过几天,村子两头双方可能又得各纠集在一起开打。
村西和村东头两波人马,白天在一起甚至在一个班上学,没有任何“仇恨”,在学校都老老实实的,不敢打架闹事。
放学回家,一到晚上两派就开始吵吵呵呵各纠集在一起,干起架来,很像当年分别支持左、右派的红卫兵。
有时他们也学电影里的“国共两党合作”,两个司令先是握手言和,两股队伍合成一股,去和我们公社相邻的石桥公社闫集生产队村子里的小孩子干架(据说是白天在湖地里割猪草,遇上后吵架结的“仇”)。
不同公社、不同生产队的小孩相互打架,可不是同一生产队的孩子们闹着玩那样“温柔”,双方在公路的地界边相遇,棍子、石块、砖头等,见什么捡起来就上去干。
还有的抱在一起摔跤,甚至用牙咬对方,双方都把对方真的当坏人、敌人看待,什么都不怕,往死里打,肯定是看什么《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战争体载的电影或连环画看多了的缘故。
5.偷西瓜
我们生产队绝大部分农田都种的是粮食作物,每年都留上五六亩地,种植一些蔬菜和瓜。
小孩子对蔬菜不感兴趣,对不能直接生着吃的南瓜也不感兴趣,唯独对西瓜眼馋。
那个年代实在太穷了,谁好好吃过西瓜?就是不太值钱的黄瓜,一年也见不上几回。
那时生产队种的西瓜,其实不是真正的西瓜,个头很小很圆,成熟后瓜子很大很多,瓜瓤是白的,水很多,但甜度低,多少年后见到了真正的西瓜,才知道那时的瓜是籽籽瓜或叫打瓜。
在新疆各地兵团团场,种打瓜很多,这种瓜籽籽很多,是专门收籽的品种,夏天到处都是不到一元一公斤的大西瓜,又大又甜,谁会去吃籽籽瓜的瓤?
但那个年代,籽籽瓜很金贵,只有生产队每年种上一两亩,到成熟时,全村每家才能平均分上最多七八个瓜。
在籽籽瓜秧刚开花时,村里的小孩早就眼巴巴地盯上了绿油油、开着满地小黄花的瓜苗了,盼望着早结出瓜来。
生产队看瓜地的老头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生产队张队长67的老爹,外号“三阎王”。
那个年代能活到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大都老态龙钟、耳聋眼花的,甚至大都病死老死了,老人年龄过六十都称高寿了。
而“三阎王”除了耳朵聋之外,身体硬朗,那半米多长的旱烟杆子从不离手,一是用来抽早烟,二是用来当棒子,看瓜地追人撵人当打人的家伙使。
谁说那个年代风清气正,都是好官?生产队张队长家大业大,张姓在生产队人口占三分之二。他当了十几年的队长,生了6个虎儿子,个个膀大腰圆,为人霸道,在村子里说一不二。
那个年代农村根本不懂不讲不怕什么法,拳头硬就是老大。张队长所仗姓多,自己儿子又多,非常蛮横,经常侵占公家财务,搞特殊化,村上的人都敢怒不敢言。
他让他“三阎王”的老爹常年担任“看青”(看生产队庄稼),拿满勤工分。这老头在湖里的瓜地里搭了个瓜篷,天天在瓜地睡大觉。瓜熟了后,不仅自己天天砸大西瓜吃,晚上还偷偷把熟透的西瓜往家里背。
生产队种辣椒、茄子等蔬菜季节,他边看守着菜地、边偷采茄子辣椒等拿回家,更过分的是把成熟的红辣椒都摘下来,在菜地边晾干后,打成包往自家运,分到社员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这老头谁得罪了他,他骂人历害得狠,因对人很凶,所以外号叫“三阎王”,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讨厌他。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和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到湖里割猪草,见到满地大西瓜,有的可能都成熟了。
大一点的小孩和我们几个小点的孩子商量,他让我们等老头在瓜地里的瓜蓬里睡觉的时候,我们去瓜地偷西瓜。
他们负责看住老头,只要老头醒来,发现有人偷瓜,大一点的几个小孩负责把瓜篷的活动门(几根棍子上面用铺的麦草扎上的)堵住瓜篷,不让老头出来,直到每人把瓜摘上跑到远处的玉米地里为止。
说干就干,大晌午天气很热,我们发现老头正在瓜篷里睡觉,六七个小孩翻过瓜地边的河堰,就到瓜地里偷西瓜,大一点的3个小孩早偷偷摸到了瓜篷后面等着了。
也不知是“三阎王”没睡着,还是几个小孩偷瓜太紧张,弄得动静太大,正当小孩们太贪心,摘了一两个在怀里兜着,还在满西瓜地里跑着选个大的拿,就听到老头突然在瓜篷里大声叫骂着,要出来赶人。
3个负责看守的大孩子,已死死地把瓜篷门堵得紧紧的,用肩膀顶住,不让老头出来,气得“三阎王”七窍生烟。
等七八个小孩每人抱了两三个西瓜跑到玉米地消失后,几个大点的小孩赶紧也逃跑了,往玉米地里再和偷瓜的那些小孩会合。
“三阎王”根本没弄清到底是哪几个调皮孩子偷了西瓜,又把他堵在瓜篷里,只能气得骂人祖宗。
那天中午,我们在玉米地里吃的西瓜最甜,尽管偷摘下来的瓜蛋子大都没有熟透……
…………………………
还有许多小时候做的糗事,因篇所限,下次再讲吧,这些小时候干过的调皮事,现在回忆起来,反倒觉得很美好,让人怀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