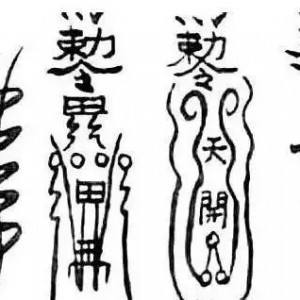无论是谈论当代诗歌,还是将其置于特殊的时空装置——如“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说话者都容易落入文学演进的老路,忽略特定的诗人,特定文本所代表的个人能力、心智能力、思维能力和写作风格在时间规律和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无论是说当下的文学现象,还是说整个中原的作家群体,都应该回归本源,从文字和语言入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作者和作者。文本的实际外观。而这就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所以,说起中原庞大的诗人群体,我想从个人和文本入手,以此为整体文学想象提供一些差异和补充。这也是我们在语言和诗歌本体论的前提下谈论的“诗意正义”和“语言伦理”,而不是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评判诗人。
诗人通过个人的历史想象、对真理的意志和精神词源,在写作中重构“当代经验”和“现实主义”,进而承担文字的“诗意正义”,是可能和必要的。每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基因”机制,而在诗人“真实话语”和“当代体验”不断加强的今天,如何将个体的实际体验转化为诗人与大众的互动空间?整体的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语言的方式通过塑造和变形将个体真理转化为历史真理,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实际上,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马新潮和杜雅两位诗人。
一
毋庸置疑,马新潮和杜雅的文风和诗意显然是个人的,从众多的诗声中很容易区分。同时,马新潮和杜雅提供了一些共同的诗歌秘诀和写作路径。这不仅与乡土知识的某些方面对诗人在日常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观察的潜移默化影响有关,也与诗人的表达方式和话语方式有关。它们都提供安静的“向下”风格写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既是个人的、具体的、时事的,又超越了个人和及时性,具有持久的力量和普遍的意义。尤其是,他们诗歌中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升华能力,使写作最终摆脱了个人审美情趣的偏见和狭隘,走向激活复杂的时空结构。这样的诗歌能够更好地让读者和研究者在时空背景下形成对诗人精神渊源和文本征兆的理解,进而以此作为衡量当代作家的尺度。
马新潮和杜雅都在寻找“诗意之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寻找命运的伴侣和心灵的朋友,也是诗人的语言责任和写作道德。“一个普通人,当他抬头看到树上盛开的花朵,看到茂盛的枝叶在风中摇曳,当他看到细雨落在地上时,他的心里可能会感到一种一种柔情或柔软,纯洁的情感会在他的心中升起,甚至会在他的心中闪现出包含希望和梦想的光。这光其实是一种‘诗意的光’。一个人的生活在小说中,总是当他不知不觉中,‘诗意的光’安慰了他,把他扶起来,一次又一次地照亮了他。” (杜亚《永远的诗光》
马新潮的诗总是让我想起钟声和平原。
在中原文化中,响铃更多地与“死”、“祭祀”联系在一起。“鸣人是村里反复示威的中心/是灵魂和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意识和历史。邝的乐器——永远逝去的哀鸣,永远沉默的声音。在马新潮的“平原”,我们会听到很多声音,真实的或虚幻的——拨浪鼓的呜呜声、木鱼的声音、“最小的噪音”、风沙的声音、雪花飘落的声音,以及家乡和外国人的呓语。更多的时候它是沉默的。“他的话越来越少,然后就只剩下骨头了。” 这是一位抛开喧嚣,逐渐沉入本土事物本质和精神的作家。诗人“以最隐秘的声音”对他们说话。
马新潮诗歌的另一个关键词和核心空间是“素”。
这个“平原”是虚幻与现实的结合,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就是“马营村”。“马营村”在马新潮的笔下反复出现,密度很高。而世代相传的人,也是“移动平原”。这片平原又具体又抽象,诗人越走越深,转身,继续疑惑,“即使站在塔顶,我也看不到我的村庄/我在塔内找到了它。那是黑暗的缝在十九楼// 一只爬行的小虫子。” 平原并非纯粹是马新潮的精神容器,更像是碎片。诗人此刻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片段粘在一起,让它们再次成为“完整的记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平原和古老的地方,
杜雅提供的是北方的《安魂曲》。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北”和“安魂曲”。
“北”涉及空间结构和地方知识。多年来,杜雅诗歌的时空语境极其个人化,具有很强的本土知识。日落或黎明,平原和山脉,森林和河流,在强烈的个人时间感中被反复观察和擦拭。这是典型的个人诗和时间诗。当我们从这些具体的事物入手,顺着它们背后的空间结构,最终会发现,一个诗人的“北方”和“中原”,既冷暖又冷。重要的是,通过对个人观点和情感体验的重新过滤、打磨、提升和变形,形成语言修辞的空间和真实的现实感。反过来,
再来说说杜雅的《安魂曲》。对许多诗人来说,写作是一种心灵洗涤和心理补偿的功能。对于有不幸童年经历和家庭财富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童年与性格和文学的关系确实很耐人寻味。作家赫拉巴尔一生都坐在童年那棵巨大的樱桃树上,时不时回首,“树枝已经升到了铁皮屋顶,有些树枝干脆趴在铁皮上。每当樱桃几乎是黑色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我从一个树枝爬到另一个树枝,一直爬到屋顶上方的树冠上,采摘了满满一手的樱桃。” (《甜蜜的悲伤》)无论我们是不断地强化和放纵我们的童年经历,还是故意化解它,它证明了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当童年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历,而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联时,尤其是当新旧碰撞时,它就更有意义了。对于杜娅来说,父亲的早逝和极度孤独的童年,让她不安和紧张。而当她终于找到诗歌的时候,她不完整的心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慢慢被弥补了。这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诗意之光”的人,而她最终完成的是一首精神安魂曲。早逝和极度孤独的童年让她感到不安和紧张。而当她终于找到诗歌的时候,她不完整的心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慢慢被弥补了。这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诗意之光”的人,而她最终完成的是一首精神安魂曲。早逝和极度孤独的童年让她感到不安和紧张。而当她终于找到诗歌的时候,她不完整的心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慢慢被弥补了。这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诗意之光”的人,而她最终完成的是一首精神安魂曲。
仔细阅读马新潮和杜雅的诗,我发现了这个时代流行词之外更深刻和隐藏的部分。他们都在低矮黑暗的地方说话,他们的作品证明了诗人与空间的语言关系以及诗人与文字的重要关系。
对诗人来说,身边的东西更靠谱,内心的质感才是最真实的。马新潮和杜雅总是把写作的重点放在那些“无声的东西”上。黄昏和夜晚成为他们更常见的诗意背景。只见,就在灯光快要关闭的那一刻,有人弯腰将阴影中的植物拉起。在天色渐暗的那一刻,他们看着那些黑暗之物的根须和土壤。或许,这就是诗人的精神寓言。
二
面对城市化语境的“中原”、“农村”、“北方”、“平原”、“河流”激发了更多的“乡愁”,而马新潮、杜雅所写的相应诗词也是“诗篇”。记忆””和“见证诗”。但是,他们的诗歌与分层的、伦理的“乡土诗”和“乡愁诗”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低级写作和一些追随者中,如此多的“痛苦”、“怀旧”和“愤怒”构成了“廉价”的伦理写作。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诗人无法描述苦难和怀旧,而是因为与此相关的诗歌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惊人,就像复制品一样。如果一首诗没有发现和创造性,但仅仅是情感的再现和对现实的新闻模仿,它还能称为诗吗?因此,对于日益流行和传播的“新乡诗”,我有些警惕。这不仅来自于大规模复制的无生命的、个性化的历史想象,也来自于这种看似“真实”、“痛苦”的诗歌类型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和增强想象。也就是说,这种诗文不仅缺乏难度,更缺乏“诚意”。读来越发觉得这些当代中国类似的诗歌所涉及的,既不是亲身经历,也不是“农村现实”,更多的诗人自以为是,一厢情愿的写作是基于想象和伦理预设的。他们不仅达不到时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而且在诗人的能力、想象力和修辞技巧上也大多是平庸的。最后,我只想提醒今天的诗人,越流行,越难。
马新超和杜雅一直在设置特殊的“精神风景”和物理知识。而他们在诗歌写作中所体现的物理科学知识更为重要,不仅是对环境、事物和细节的重新发现,而且对发现和创造文字的能力的诉求。从这些封闭、半封闭或开放空间中事物的细节出发,那些自然的事物与诗人的内心,往往相互呼应或矛盾,相互摩擦、不同意、相互碰撞。马新潮和杜雅的诗歌呈现为时间体验与内心冥想的精神对应。他们在表达平原(农村)和城市等空间主题的同时,也对农村的流失和城市的扩张有着担忧和痛苦,同时,他们关注个体生命的深处——存在感、暂时的焦虑与和解、在人生单行道上的茫然沉思与解脱对话。这一定是一首关于生命和内心自我的“时间诗”——如马新超的《在我的小心里/也住着上帝的气息,经过/无数次雷击/也像这暮光陡峭》(《法王》寺、久保”),如杜亚的“我必须爬到远离世俗和庆典的地方/不再被风景变化的光线所诱惑/我必须在日落之前到达/-在它腐烂和消散之前/因为一切都如黎明的曙光一样出现:/到达那里,就是到达万物的精神/到达那里,到达纯净之地”(“
焦虑、孤独、痛苦,并不是单纯的城市化时代带来的“离家之感”,而是我们在本土知识流失过程中无处可去的“精神家园”。我们将继续在文本世界中寻找在文化地理上越来越模糊的基因和根源,寻找我们失落的文化童年和前现代当地经验的摇篮。这是诗人对“根本”存在的追寻和回归,尽管我们正在寻找我们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新潮和杜雅想要做的,就是在寂静的深处寻找。在这些不再是时代焦点的场景和细节中,诗人意外地同时遇到了历史和现实。这些场景和细节既是记忆中的历史,又是精神穿透的现实和当代。这种看似日常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成为当代中国诗人叙事的宿命。对本土知识和弃物的追寻,其实就是回归“精神主体”的过程。这种知识不是地理和地域的旅游手册,而是与出生地、家乡、家乡中国、生活史和成长史的真实关系。精神见证的历史融合在一起的精神胎记。这就需要个人的历史想象——只有对场域的开放概念,才能将历史、现实和个人融合在文字的世界中。
三
长诗最能检验一个诗人的整体写作能力,这是对语言、智力、精神力量、想象力、感性、判断力,甚至体力、耐力、精神力量的最彻底、最彻底的评价。综合测试。马新潮和杜雅都擅长写长诗。
中国新诗100年,诗人写作的信心明显在不断提高,许多沉迷诗坛多年的诗人也在不断尝试写长诗。这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诗意力量,也是为想象的诗意历史和地理搭建一座灯塔或纪念碑,供同时代和后人观看。的确,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几乎是全方位的、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质感和整体结构上出现任何错误和疏漏。现代化的历史想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我们也要给一些爱写长诗的诗人泼一盆冷水,因为从中国诗歌传统来看,长诗不一定是衡量一个诗人重要程度的首要指标,甚至一些短诗也可以流传下来。诗和它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句子。1980年代的江河、杨濂、常瑶、海子、罗一和,1990年代的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等在长诗创作上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响应者很少。从198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其中不乏现象级的。但平心而论,许多诗人和评论家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长诗的能力和耐心,尤其是一些巨大的长诗让专业读者望而却步。过去长诗一般都有一个整体的结构,否则很难建立,如神话原型、英雄传说、民族史诗等。然而,随着近年来诗歌文化整体结构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即刻感受的片断,长诗的创作可能面临相应的挑战甚至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整体结构,一首长诗应该通过什么来完成?甚至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很多长诗都是在偏执狂和文学史野心的推动下草草创作的,而且大多是半成品和有缺陷的,而一些所谓的长诗只是在欺骗和误导系列。短诗只是放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是即刻感受的片段,长诗的创作可能面临相应的挑战甚至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整体结构,一首长诗应该通过什么来完成?甚至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很多长诗都是在偏执狂和文学史野心的推动下草草创作的,而且大多是半成品和有缺陷的,而一些所谓的长诗只是在欺骗和误导系列。短诗只是放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是即刻感受的片段,长诗的创作可能面临相应的挑战甚至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整体结构,一首长诗应该通过什么来完成?甚至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很多长诗都是在偏执狂和文学史野心的推动下草草创作的,而且大多是半成品和有缺陷的,而一些所谓的长诗只是在欺骗和误导系列。短诗只是放在一起。而且大多是半成品和有缺陷的,一些所谓的长诗只是在欺骗和误导这个系列。短诗只是放在一起。而且大多是半成品和有缺陷的,一些所谓的长诗只是在欺骗和误导这个系列。短诗只是放在一起。
但杜雅的《秋花》、《北极星》、《天上城》等多首小长诗,却表现出极强的介入时代主题的能力和能量。这些诗篇也更全面地展示了杜雅的整体诗歌能力,既能写出个人诗,又能在个人基础上发展整体诗、见证诗。显然,这样的诗是沉重的。就长诗的创作而言,马新潮的《魔河》也代表了高水平。“黄河”是宏大历史、民族和人类的隐喻,也是诗人整体的精神进路和想象空间。马新潮的《魔河》是一首精神与思想的诗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是诗人的精神家园,是“
马新潮和杜雅成功的长诗创作实践,使我们认为诗歌不仅是“个体诗”、“当下的诗”、“片面的诗”,更是时空同步意义上的总诗。和精神命运共同体。整体的诗歌乃至人类的诗歌,当然后者是建立在个性、生命和存在的前提之上的。
中国诗歌热切期盼更多普通诗人的出现。

本文发表于2019年5月22日河南日报第14版,为《中原风文艺评论》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