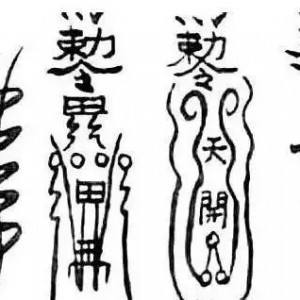“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大规模融化。短视频正在取代电影,笑话正在取代小说,短评正在取代批评。为它辩护的虚弱形式,世界的支离破碎的表达,现在已经改变了——如果你有一百万的追随者,不管你有多矮,你都是神。”
在第五届“沪宁双城文学研究会”现场,作家陆内朗读了自己写的小说。对于这次以“文学与公共生活”为名的聚会和讨论,这段话似乎是一篇精彩的评论。
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和《探索与争霸》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沪宁双城文学研究研讨会”在上海富轩宾馆举行。除了来自上海和南京的年轻评论家,与会的还有作家陈念熙、作家杜丽、作家郭爽、学者黄登、“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腾讯科技有限公司游戏策划人。汉服,作家陆内,作家三三,作家双翅目,剧作家文芳义,学者严飞,学者周立民,《花城》客座主编朱燕玲等 黄屏,华东中文系教授师范大学《长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向静主持。
有趣的是,这一天,福轩酒店至少同时举办了三场研讨会。分别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政治学系和哲学系主办。在主题设置方面,三个学科分别举办了不同的研讨会。这些活动都与“公共生活”有关。
“在这样一个讨论文学的地方,我读了我的小说,想为小说的名字辩护。”陆内打趣道:“今天,小说似乎越来越‘非公开’了,非小说文本成了‘公开’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有‘公共非小说’,我们有‘私人非小说’。 ,' 还有另一种,叫做'影响者非小说'。”
第五届“沪宁双城文学研修班”现场。本文场景图为谢世豪图片
每个特定的人构成了时代的图画
“在路边,我可能是‘公共散文’。但我会说,当我写那些散文时,我什至没有意识到这是‘散文写作’,我只是感到受到启发,觉得我有话要说。” 《地球上的一家人: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农村山水》作者、学者黄登说:“有人说我只写底层的人,农村人,二本学生,还有人说我“选”了一个特别好的IP,我不认同。我是农村媳妇,在二本学校教书十多年。不需要选择任何东西。我写的是我生活半径中的人和事。”
2016年伊始,黄登的文章《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田园风光》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直接让原公众号的粉丝增加了3万多。 “因为涉及到我家的人和事,所以我特地问了我老公才发,他不同意也不拒绝。后来发的时候,我说我把家里的事情记下来了,但是他说不是。因为大家(农村人)都是这样的。后来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的评论,真的很感动。当时没想到他们是人在屏幕后面。我以为他们都是我周围的人。”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认为个人经验可以与公众经验联系起来,关键在于个人能否代表一群人。 “其实我们这群‘70后’从小就见证了中国的各种变化。我们的个人经历与时代同步,所以社会的每一个过程都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黄灯和路
在陈念熙的理解中,“文学与公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不应该是炙手可热的生活。 “每个人的存在不一样,经历不一样,面临的生活也不一样。比如南方人,北方人,农村人,城市人。作者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命运。把这些整理好,是一个时代。图片。”
从1999年到2015年,陈念熙当了16年的矿工。 2016年,诗集《爆炸》获首届工人桂冠诗人奖。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诗国?因为我们普通人通过诗歌了解历史,了解时代,了解世界人民。”陈念熙说,当下的诗人很有自信,确实有诗人写出优秀的诗篇。几千年的诗歌史和世界诗歌格局,我们其实是很弱的。 “比如在最早的《三百首诗》中,我们可以从《风》中看到远古时代的爱恨情仇,看到人和人。比如,从杜甫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中唐的民生政治,以及那个时代的变迁。我们今天的诗歌,除了技巧和浪漫爱情,几乎是一片空白。”
除了诗歌,陈念熙还创作非小说类作品。今年,新的非小说作品集《活着就是向天空呼喊》和《微尘》。他坦言,人很难做超越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非小说写作是他所经历、见证和思考的——他在矿井里的生活,他和他的同事的命运,以及家乡的风风雨雨。他也希望这个时代能给非小说更多的机会让它成长。
曾在南方周末等媒体担任专题撰稿人的雷雷深信不疑:“我已经从媒体人变成了半文人,或者做过一些跨界的创业工作, “希望成为更好的人。普通人与文学之间的桥梁,让纪实作家得以生存。”
2016年,正式创立非小说类自媒体平台“真实故事计划”。 “‘真实故事计划’的设立是为了推动非小说类的普及——更多的人写作,更多的人阅读。”雷磊表示,在“真实故事计划”中,公众可以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来表达。 ,他们在头三年收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 40 万条文字故事。
他说,在平台的运营中,他们会用选题的方式来挖掘文本,希望每部作品除了是好文之外,它的主题也能引起更多关注,或者打到圈里的人。当今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些痛点。只有这样,很多作品才能摆脱自娱自乐的困境,真正走向大众。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不属于文学体系的作家来说,他们希望提供一个被现有严肃文学所忽视的渠道和平台,帮助更多的普通作家继续写作。

陈念熙
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建立在真诚的理解之上
“文学不应过多干预公共生活。”
思南文选副主编黄德海的第一句话,就让大家大吃一惊。然后他说:“我不是说文学不应该是关于公共生活的,两者是有联系的,但一定是你感受最深的部分。它其实是扩展了公共生活的某个点,而不是故意与公共生活建立起共谋或过度友好的关系如果你想干涉公共生活,可以,但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有时文学家长期呆在室内,不知道公共生活的复杂性。出门后扰乱公众生活。”他强调文学永远离不开公共生活,但两者的关系应该建立在文学对公共生活的真实理解之上。
在写小说之前,郭爽做过十年媒体人。 “新闻写作也是一种非虚构的形式。当时我们有一句流行而残酷的说法,‘转身就忘了’。就是你关掉录音机,拿走被采访者的财物。有一个很微妙的这里的道德准则——你如何选择?你如何判断别人的东西是否可以直接为你所用?你真的了解他吗?我这里所说的了解是一种真正的同理心了解。”
她想起了在贵州贫困县做低级公务员的表弟。他虽然忙于生计,但仍有空闲时间看小说。一天,一个和她表姐在同一个乡镇,初中文化的小伙子突然问她:你看过电影《坐地上的大象》吗?郭爽说还没有看到。年轻人又说:我看了,第一次看不懂。我一共看了三遍。我觉得他(胡波导演)很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震撼感受。我觉得人们在讨论文学的公共性时,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文学不是需要仰望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需要拯救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的很多角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存在。”郭爽说:“像我表哥这样住在城镇和乡村的年轻人,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学或小说之类的词。别人可能总是难以理解。也许我永远不会写他们,但我觉得如果我想写,我要懂,而且真的懂。”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学首先应该有一个理论框架,但我认为社会学家是一个能先讲好故事的人。”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闫飞最近特别关注了那些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相交,但生活经历却不为我们所知的农民工。苗族《奇葩说》中的19岁橱窗工,加入皮村文学团的社区保安,遭遇校园欺凌后去新发地帮妈妈卖菜的女孩……

“讲故事的人的职责是创造更多的空间,让看不见的事实看得见,同时不断探索理解背后的不可理解的可能性。”闫飞说。
参与作家的作品
与其想象,不如让自己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坊召集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进特别提到了工作坊海报的两次改版。 “看了初稿,有点忐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有点像香港,有点像上海,总体感觉是比较都市化,比较精英化,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问了我的同学,即使是在上海,能不能找像石库门和新村这样的背景照片?”
提出二稿后,金立立刻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在思考公共生活的时候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为什么要刻意在城市化和精英的画面中做一些区分?似乎他心目中的公共生活不再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公共生活似乎包含着一种伦理的包袱。
随后的二稿不仅改变了城市街景,还增加了一个窗口。 “如果阿伦特描述它,公共生活就是城邦,或者说‘窗外的世界’,”李金说。 “而窗户似乎暗示着一种目光。窗内私人领域的文学作品构成了窗外更广阔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海报
在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看来,“公共生活”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或公共生活,“公共”与“公共”与“集体”之间存在距离,“所以-叫公共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由方格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很多普通人的故事。”

他说,一个文学人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想象一个与我们相反的公共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谈论底层或劳动人民会带来罪恶感和羞耻感,并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或文化人,我们应该怎么做,但这正是文学需要警惕的公共生活。相对于个人生活来说,是一种超然的存在,对于书院里的人来说,农民工的生活可能是一种公共生活,但相对于那些工作的人来说,加缪和毛姆一起读加缪代表着公共生活。 "
他还特别提到了上海的读书会。各类读者之所以愿意放弃休息时间来到公共场所,是因为他们希望听到一些超出自己生活经历的东西。 , “他们想从他们的私人住宅走到一个广场,他们的生活被称为公共生活。而这种公共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创造的。”
江苏省作协创新研究室副主任韩松刚也分享了他对当下文学生态的观察,指出现在很多所谓的公共生活都是“伪公共生活”,或“异化的公共生活”。 “我们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往往是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在这种公共生活中,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有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和维护,有理性的公共秩序。如果同时存在几个条件,它们只能在写作的层面上进行创作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这与文学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有关,这就是文学的‘积极’一面。”
但他强调,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文学本身的局限性。例如,非小说写作具有很强的公众意识。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这是一种“片面”的宣传,因为它往往面临着个人被压制、价值观被抛弃、秩序被破坏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代表真实公众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性和公共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这是文学参与或表达公共生活的‘消极’方面。”
《上海文化》主编木叶认为,真正的公共生活其实无处不在。它是与这个世界的超链接,无限地与无数的人、事、事联系在一起。不迎合它就无法避免,或者说,每个人天生都承载着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作家的才华在于塑造它。这个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首先是发现自己的局限,包括发现自己的“不敢”和“不能”。
鲁迅说过,人的灵魂是没有联系的。但木叶认为,在这种不相容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文学的魅力在于试图表现出灵魂之间的微妙联系,这种联系虽然没有联系,但可能存在。”
上海思南书友会,读者排队入场。 (思南读书会供图)
重构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对话
帕慕克说:“我生活在一个始终尊重高级官员、圣徒和警察的国家,但拒绝尊重作家,除非他们上法庭或入狱多年。所以我将受到审判对我自己来说,可以这么说。不要太惊讶。我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在笑着说我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在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大众生活中的文学形象,或者说大众对文学的期待。
他直言,如果从“经典文学”的角度来谈,现在的文学缺乏某种冒犯。 “最具活力的文学往往是进攻性文学。进攻性是对文学自我的侮辱,也是对公共生活的侮辱。例如,《尤利西斯》曾被认为是除文学之外最危险的书。规则也是冒犯社会意识。即使在今天,这种冒犯还没有消失。”
但他认为,中国文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驯化”的状态,“我举几个现象,目前出版界的选题论调是一门典型的学科,符合基本预期,让作家发生变化。基本的期望达不到,就干脆被排除在外。即使是当下最活跃的奖项,团结和纪律也越来越强,可见一个作家总能赢得各种文学奖项。”
照片
《思南文学选刊》副总编方燕认为,我们谈“文学与公共生活”,其实是在谈文学的公共性,属于“什么是不足,只谈”。 “在这个行业诞生的时候,宣传是一种自然属性。今天的文学作品缺乏宣传,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说,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界开展了自己的研究。三个“操作”,一个是纯文学的概念,一个是人文精神的探讨,一个是学院派,“这三个“操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遮羞布,它是一种自我阉割,自我局限、自我消弭我们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身体里复杂丰富的东西都被格式化了。关于文学的宣传,那将是一条死胡同。”
“199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学家谱的文学与大众生活越来越疏远。尤其是21世纪以来,很难在1980年代看到这么多现象级的文学作品。文学被赋予参与公共生活、促进民族审美和社会进步的责任不断下降。”研讨会召集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说。
在他看来,今天的文学在表面上扩大了界限,但以流为中心的泛文学写作也在淡化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拥有最多读者、被资本定义的网络文章,当然是承载了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但要问网络文章的思想审美贡献有多大?而且,个人写作在1990年代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审美自立和自律,但也带来了其固有的局限性:过分关注自我,切断了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尽管文学确实做到了。不一定要回应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但如果公共事件和公共问题一般被排除在作者的视野之外,那是极其不正常的。 “总之,在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今天,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如何重建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值得我们关注。更多的关注。思考。”
工作坊召集人、《探索与争霸》杂志主编叶竹娣也表示,文学是衡量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精神诉求的活动,为城市公共生活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同时,它也衡量城市公共生活的精神品质及其优劣。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文学与公共生活,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对话,呼唤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精神意识,同时也在自省与自信的双向维度,重建文学与地球. ,希望的哲学和将文学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