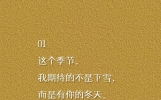一首歌火了,是铺天盖地的那种火,是刺人眼目,如雷贯耳的那种火。
一刹那间,各种网红争相模唱,所有曲种尽数勾新。总之就是火的一塌糊涂,火的遮天蔽日。
这是一首初听逗人一笑,再听难解词义的歌。
歌词引经据典,巧用隐喻,开腔看似骂人,却又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引述古老的故事,又是写真,又是夸饰,铺垫中含有真情,吟咏里全是愤怒。无厘头的幽默,给人留出无效想象的空间,苍老的传说在新时代焕发出灿然的生命力。
歌是火,可以温暖,也可以焚毁。歌是电,可以发光,也可以劈摧。沉静闲适里绽放光芒与鲜艳,激越昂扬中展示不屈与力量。
美与丑的争斗,也是文学永恒的话题。这首歌,超越身份约束,突破概念圈定,你可以贬他是睚眦必报,也可以赞他是点亮心灵。传统文化是他的台阶,勇气,智慧,独具魅力是他的旗帜。嬉笑怒骂尽显文化,放歌天籁皆是精彩。
请你将罗刹海市当做一首诗,其实他本身就是一首诗。
这首诗,可以上追诗经之写实,可以溯源离骚之浪漫。
这首诗,必将列序文坛,载名青史,让我们的后人在阅读或者聆听之后,再不敢轻视我们这个时代。
附:罗刹海市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过七冲越焦海三寸的黄泥地,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
河水流过苟苟营,苟苟营当家的叉杆儿唤作马户,十里花场有浑名。
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腚,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卧。老粉嘴多半辈儿以为自己是只鸡。
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
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他叫马骥,美丰姿少倜傥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
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
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
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
爱字有心心有好歹,百样爱也有千样的坏。女子为好非全都好,还有黄蜂尾上针。
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他言说马户驴又鸟鸡,到底那马户是驴还是驴是又鸟鸡,那驴是鸡那个鸡是驴那鸡是驴那个驴是鸡,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