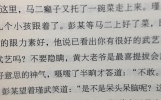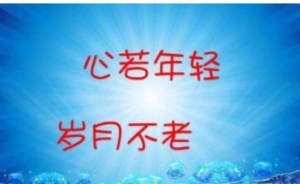余秋雨形容母亲勇敢、美丽、谦虚、腼腆、聪明、宽容。
余秋雨称自己毕生的大胆,从根子上说,都来自于妈妈。“十几年前我因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密布着恐怖主义危险的人类古文明遗迹,被国际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实那每一步,还是由妈妈当年温热的手牵着。”
下面是余秋雨关于母亲的文章和一些日记,细细品读,情真意切。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余秋雨
1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我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成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儿紧张,害怕因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2
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商量,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3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3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3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无数次命悬一线。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所以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过那两座山岭回家。
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后来我因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的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余秋雨:伺母日记
字字真情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余秋雨。
●2012年11月18日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请假。对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我这门课,没法调。”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不要对老人作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蔽。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2012年11月19日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但这一对年轻夫妻少想了一个关键问题:家乡没有学校,孩子出生后,怎么完成最基础的教育?这孩子,就是我。
妈妈的头发在今天的病床上还只是花白。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亮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她的这头头发,清扫了家乡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文盲荒原。
妈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她幼小的儿子。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她的幼小儿子一进去,就被发现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原因了,因为小孩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代价”: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2012年11月20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花签蘸清水湿润她的嘴唇。从她小小的嘴,我想起,她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在一个个极端困难的灾难中,竭力让全家那么多嘴,还有一点点东西吞咽。这个事业,极为悲壮。
1962年经济稍微恢复,我还因饥饿浮肿着,有一天妈妈要我中午放学后到江宁路一家极小的面店去。那儿开始有不凭粮票的汤面供应,一人只能买一碗,8分钱,浮着数得出的几根面条,但是,排队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队伍长到半里路。我放学后到那里,妈妈已经端着一碗汤面站在那里等我。
妈妈的右手在输液,我一次次摸着,还是温热的。“文革”中,我爸爸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顿失经济来源,我还在学校受造反派批判,已经没钱吃饭。那天妈妈来了,叫着我的小名,就用这只右手握着我的手,我立即感觉到,中间夹着一张纸币。一看,两元钱。
很快,我通过侦查,实地看到了这钱的来源。妈妈与其他几位阿姨,到一家小工厂用水冲洗一叠叠铁皮。她们都赤着脚,衣裤早已被水柱喷湿,那时天气已冷,而那铁皮又很锋利。洗一天,才几毛钱。上次她塞在我手里的,是她几天的劳动报酬。想到这里,我又用手,伸到病床里,摸着了妈妈的脚。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我们把一条小毯子加在她的肩头。肩头,又是大量回忆。“文革”中我好不容易从农场回家,刚上楼梯看到一张桌子在自己移动,原来是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下面用肩膀在扛。家人死的死,关的关,走的走,没有人为她搭一把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写了那么多书,后来又担任了高校领导,但宿舍的老邻居都还记得,每天肩上搭着灰布食物袋来为我做饭的,还是年迈的妈妈,后面还跟着爸爸。现在学院很多人还在深深缅怀那个时代的工作成效,出版社也在抢着出那些老书,其实一切都与妈妈的肩膀有关。
爸爸经历九死一生终于活到了“文革”之后,最终,却因为读到了那些诬陷我的报刊而极度愤怒,离开人世。他临终床头那3份划满了颤抖红笔的报刊,我永远不会忘记。
妈妈曾经一再劝说爸爸不要去看那些报刊。爸爸说:“岂能让魔鬼再疯狂。”妈妈说:“魔鬼的事,与我们无关。”由此可知,“魔鬼”是靠着爸爸这样的人成事的,面对妈妈,他们束手无策。我身上,既有爸爸的成分,又有妈妈的成分,后者更多一点。
●2012年11月22日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让意识恢复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二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是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二星期?
我看一个人是否体面,标准有几十项,其中有三项与生命的句号有关:一、有没有可能拒绝“残忍抢救”?二、有没有可能在被追悼时只穿平日喜欢的那套服装,而不是统一的“寿衣”?三、有没有可能在生前就拒绝在墓碑上刻写官职?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三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加持。我妈妈也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三次了,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2012年11月23日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同时得了天花,村里的“仙姑”已判定必死。妈妈早已心灰意冷,手足无措。祖母听说荸荠能凉火,但季节不对,只能迈着小脚去敲一家家农舍的门,一直敲到6里路之外的那一家才买到几个风干的。刚进村,听到了我的哭声……活下来,太偶然了。
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为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这使我每次遇到那些哀怨连连或戾气冲天的人群,总会在心里说:你们其实是活得太容易了。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我后来因贴地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时刻。
有两位学者根据我的各种记述作出研究,认为我妈妈在我童年完成了“从人格到能力的全方位教育”,“似土实高”、“似浅实深”,值得今天的万千家长省思。其实,我妈妈对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似无实有”,完全出于“爱的自然”、“生的无意”,毫无有关输赢的盘算。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昨天呼吸急促,今天又回到了常态。这平静的眉眼,我最熟悉。连她的勇敢,也平静得不像勇敢。灾难年月中我的几次勇敢,例如为了一个文学杂志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组织上海唯一的周总理追悼会等等,妈妈都知道。她说:“大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灾难过去后,大小暴徒被驱逐,妈妈牵心了10年的爸爸和叔叔均获平反,但她一点儿也不激动。我受到自己单位的广泛拥护,选为院长,她也毫无表情。我生日那天,马兰打电话给她,认真而全面地告诉她,她生了一个很不错的儿子。她平静地听完,只笑问一句:“今天弄点什么吃?”
妈妈的人生有禅意,又更近道家,可能是受了外公的影响。把什么都看穿了,因此只在乎很确定的小事,不在乎不确定的大事。平时在餐桌上,我们经常会为“大事”而气愤,妈妈假装听不懂。等我们稍稍一停,她立即问起生活小事,让我们自嘲刚才的激动。
与妈妈相比,爸爸更近儒家,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妈妈觉得爸爸“心太重”。其实,这也正是儒家的共通毛病。妈妈除了本性善良外,几乎不信任一切理念、等级、界线、规范。受她影响,我“立道佛而近儒墨”。
●2012年11月25日
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20岁开始,我每次要作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脸色,似乎退去了一层灰色。我和马兰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马兰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后记:2012年12月9日凌晨,余秋雨92岁的老母亲去世。骨灰将在今年清明送往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与10年前去世的余秋雨父亲安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