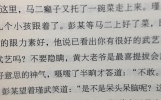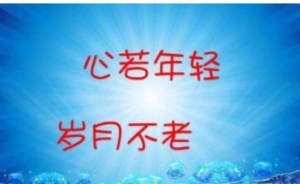莱伊·布拉特伯利
安娜·泰勒小姐已经24周岁了,鲍布·斯波尔丁也快14岁。那年夏天,安娜小姐来格林镇中心区任教。她是个受人尊敬与爱戴的老师,孩子们都想送给她礼物,譬如大桔子啦,粉红的鲜花啦。夏日来临,万物茂盛,橡树和榆树蓬盖似的枝叶把林荫道变成了暗绿色。在这样的日子里,她好象总要在林荫路漫步。人们都说,她是寒冬的硕桃,是酷夏的凉奶。是的,那些日子是少有的,气候凉爽宜人,微风习习吹拂着树叶。那些日子就像安娜小姐一样美好,那些日子本来应该以历法的形式用安娜的名字来命名。
在每年10月的夜晚,鲍布·斯波尔丁也独自在镇子里漫步,背后散落着一片片树叶,就像一群万圣节前夕的耗子。或者你会看见他像一条淡白色的鱼儿在狐山小河的酸水里被烘烤成棕色。或者你会听到他在微风吹拂的树顶上的哨声,然后他又从树顶上攀援而下,独自坐在树蔸旁,观看这个世界。
第一天上午,安娜·泰勒小姐来到教室,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课后,鲍布提来一桶水洗黑板。
“这是什么?”安娜从讲台转向他,她正在那里收拢拼音作业本。
“黑板有点脏。我想我本来应当问问可不可以洗黑板,”他吞吞吐吐,有点不安地说。
“我们可以假设你问过了,”她笑哈哈地说。这时他已很快地洗完了黑板,用力拍打着黑板擦,空气中飞扬着白雪似的粉笔灰。
第二天上午,他站在她宿舍的外面。她从屋子里出来了。准备去上课。
“喂,我来了,”他说。
“哦,你知道我可并没有感到意外。”她说。
“我能帮您拿书吗?”他问。
“可以。谢谢你,鲍布。”
他们一起并行,走了好几分钟,但鲍布一直沉默无语。她瞥了他好几眼,轻轻地碰了他一下。这时她看到,他是多么自在,显得多么快乐。当他们快到校门口时,他开了:“我最好先走,要不然那些小孩子会不理解的。”
“我实在不懂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泰勒小姐说。
“怎么啦,我们是朋友呀,”鲍布说,带着一种天真的诚实。
“鲍布——”她说。“不要紧。”她走了。
以后的两个星期,他在课堂上和课后都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洗着黑板,而她在旁边教课,太阳安祥地从低低的天空照耀大地,只听见翻书的沙沙声和写字的瑟瑟声。有时这种寂静会持续到下午5点,这时泰勒小姐会发现鲍布坐在最后一排,在那里等待。
“好了,该回家了。”泰勒小姐说。这时他会跑上讲台,替她拿帽子和大衣。然后他们会横穿那空荡荡没人的院子,边走边天南海北地交谈。
“鲍布,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当作家,”他说。
“噢,那可是个不小的理想。”
“我知道,我将努力去做。”他对她说。“我读了许多书。”
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泰勒小姐,您能帮我吗?”
“那得看情况。”
“每星期六,我都沿着小河走到密执安湖。那里有许多蝴蝶和小龙虾。或许您也喜欢散步。”
“恐怕我不喜欢。我很忙。”
他本来想问她忙些什么,但他没有问。“我带了些三明治和汽水。希望您能来。”
“谢谢,鲍布。恐怕这会儿不行。”
“我不该问您,是吗?”他说。
“不,你有权利问任何你想问的事,”她说。
几天后,她给了他一本《远大前程》。他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他们一起谈论这本书。
鲍布每天都碰到泰勒小姐。好几天,她想对他说以后别再来,但她终未能说。
在上学的路上,他和她一起谈论着狄更斯,谈论着吉卜林和爱伦·坡。但她不可能在课堂上叫他背诵。她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叫别人背诵。他们交谈时,她再也不会瞥他了。但是,在好几个傍晚,他手臂使劲擦着黑板,把黑板上的算术符号擦掉,这时,她觉得自己不自觉地瞥了他好几眼。
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他站在小河里,高卷裤脚,弯腰捉小龙虾,突然看见她来了。
“喂,我来了,”她说,哈哈大笑。”
“你可知道,我也不感到意外,”他说。
.“给我看看小龙虾和蝴蝶,”她说。
他们走到湖边,坐在沙滩上,暖风温柔地吹拂着他们,扬起了她的秀发和罩衫上的褶边。他在离她几码远的地方坐下。他们吃着夹有火腿和泡菜的三明治,并一本正经地喝着桔子水。
“我没有想到会来这样的地方野餐,”她说。
“还与某个孩子在一起,”他说。
整个下午,他们很少说到别的事情。
“这全错了,”鲍布说。“我也不知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往前走,捉蝴蝶、小龙虾,吃三明治。要是父母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笑话我,其他小孩子也会的。而其他老师会笑话你,是吗?”
“我想恐怕会的。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来这儿,”她说。
安娜·泰勒小姐和鲍布·斯波尔丁相会时的所有东西就是:两三只橙褐色的大蝴蝶、一本狄更斯写的小说、几十只小龙虾、四块三明治和两瓶桔子汁。
星期一,虽然鲍布等了很长时间,但还是没见泰勒小姐来到学校里。她提前走了。那天下午,她头疼,因而很早离校。
星期二放学后,两人又相对无言地坐在教室里——他心满意足地去擦黑板,她则默默地批改作业。突然。县政府大楼的钟声响了五下。那铿锵的铜质钟声使人震颤,使你感觉
到时光的流逝,使你逐渐变老。泰勒小姐搁下笔。
“鲍布,”她说,“过来。”
“嗯。”他放下黑板擦。
她注目凝视着他,直至他把目光移开。“鲍布,我想你是否懂得,我会对你说些什么。”
“嗯,”他终于开口了。“谈我们的事。”
“你多大了,鲍布?”
“快14岁。”
“你知道我有多大吗?”
“嗯,我听说过。你24岁。再过10年我也24岁,”他说,“有时我好象是24岁的人。”
“是的,有时你几乎真的像24岁的大人。”
“确实是这样!”
“请坐,安静点。我们要明白我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这很重要。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朋友。我以前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学生,也没有对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像对你那样动过感情。”他对此有点脸红。她继续说:“我敢说一一你已感到我是你所认识的最好的老师。”
“噢,比你说的还要好,”他说。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小镇和居民,还有你和我。我已想过了,鲍布。不要认为我没有意识到我的情感。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的友情有点奇特。但你是个不平凡的孩子。而我知道,我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都是健全的,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对你的性格和德性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要考虑的事情,除非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成年男人,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如果我再大10岁,再高15英寸,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两样了,”他说。
她说:“我知道,当你感到你是个大人,感到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荒唐可笑了。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如此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思想,以致于他们会说,‘这是一个男人,虽然他只有13岁,却认识到了一个成人的责任’。但要做成人,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里还必须增加年岁,增加高度。”
“我不希望如此。”他说。
“我可能也不希望,但是关于我们两人的事情真的是别无他法。”
“嗯,这我知道。”
“我们必须决定还有什么事要做。”她说。“我能保证调离这个学校……”
“你不必这样做,”他说。“我们家要迁移了。我及家人要移居麦迪逊。”
“对所有这些事情就无计可施了吗?”
“不,不,我父亲在那儿找到了一个新工作。那地方离这儿仅50英里远。我会来看望你的,不行吗?”
“那会是个好主意吗?”
“不,我想不是,”他说。
他们坐在寂静的教室。
“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没有人会知道的。人们几千年来都不知道。有时两个人互相喜欢,但他们不应该。我不能解释这件事。”
“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记住,”她最后说。“在生活中会有补偿。你现在感到烦恼,我也一样。”“但会有东西来补偿这一点的。你信吗?”
“但愿如此,如果你愿意等待我的话,”他脱口而出。
“10年?”
“那时我24岁。”
“但我却34岁了,很可能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我认为这不可能。”
他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说。
“你会忘掉的。”
“我要千方百计地永远不忘记你,”他说。
她去擦黑板。
“我来帮你,”他说。
“不,不,”她赶紧说。“你还是回家去吧。”
他走了,离开了学校。他回头瞻望,透过窗户,只见泰勒小姐伫立在黑板边,慢吞吞地擦黑板。
他第二个星期就搬走了,这一走就是16年。虽然离格林镇仅50英里远,但直到他近30岁结婚时,他才重回格林镇。那是个春日,他们夫妇俩驱车前往芝加哥,路过格林镇。他们在那里停了一天。
鲍布让妻子留在旅馆,然后他独自一人在城里游逛。最后才问及安娜·泰勒小姐。
“噢,那位漂亮的老师。她在1936年就去世了,就在你走后不久。”
“她结过婚吗?”
“没有,她从来没结过婚。”
他从学校出来,来到公墓,找到了泰勒的墓碑,上面刻着:“安娜·泰勒,生于1910年,卒于1936年。”26岁,唉,泰勒小姐,我现在几乎要比你大4岁了。
那天傍晚,人们在小镇子里看到鲍布·斯波尔丁的妻子。人们都说,她是寒冬的硕桃,是酷夏的凉奶。是的,那是些少有的日子,气候凉爽宜人,微风习习吹拂着树叶。大家都认为,这一天本来应当以鲍布·斯波尔丁妻子的名字来命名。
(陈小平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