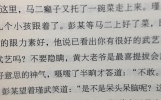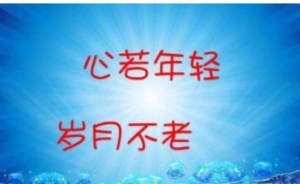那是40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傍晚,大人们都在外面摇着扇子聊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流着汗看书,那是我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正读得如痴如醉时,书从我手中被拿走了,是父亲拿的。我当时有些紧张,但父亲没说什么,默默地把书还给我。就在我迫不及待地重新进入凡尔纳的世界时,已经走到门口的父亲回头说了一句:“这叫科学幻想小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决定了我一生的名词(“科幻”这个简称则要到十几年后才出现),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惊讶,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故事是真的!凡尔纳的文笔十分写实。“这里面,都是幻想的?”我问道。
“是,但有科学根据。”父亲回答。
就是这3句简单的对话,奠定了我以后科幻创作的核心理念。
以前,我都是把1999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科幻创作的开端,到现在有20多年了,其实,我自己的创作历程要再向前推20年。我在1978年写了第一篇科幻小说,是一个描写外星人访问地球的短篇。在结尾,外星人送给主人公一件小礼物,是一小团软软的可以攥在手中的薄膜,外星人说那是一个气球。主人公拿回去后向里面吹气,开始是用嘴吹,后来用打气筒,再后来用大功率鼓风机,最后把这团薄膜吹成了一座比北京还大的宏伟城市。我把稿子投给天津的一份文学刊物,然后如石沉大海没了消息。刘慈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我和父亲那3句对话所构成的传统科幻理念已经开始被质疑,然后被抛弃,特别是在后面的那10年中,新的观念大量涌入,中国的科幻创作则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这些观念。我感觉自己是在独自坚守着一片已无人问津的疆土,徘徊在空旷的荒野中,那种孤独感,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过曲线救国,写出了像《中国2185》和《超新星纪元》这样的作品,试图用边缘化的科幻赢得发表的机会,但在意识深处仍坚守着那片疆土。后来我放弃了长篇小说的写作,重新开始写短篇,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幻理念上来。
开始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后,我惊喜地发现,原来这片疆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空旷,还有别的人存在,之前没有相遇,只是因为我的呼唤不够执着。后来发现这里的人还不少,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再到后来发现,他们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大家共同撑起一片科幻的天空,也构成了我科幻创作的后15年。
科幻文学在中国有着不寻常的位置,作为一个文学类型,它所得到的理论思考,所受到的深刻研究和分析,所承载的新观念、新思想,都远多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新的话题和课题在不断涌现,不断地被研究和讨论,没人比我们更在意理论和理念,没人比我们更恐惧“落后于前卫”。
曾经有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以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是一块砖一块砖地垒一堵墙;而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则是一架梯子,一下子就能爬到墙头的高度。
这种说法很好地描述了科幻界的心态,我们总想着要超越什么,但忘了有些东西是不能越过的,是必须经历的,就像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我们不可能越过这些岁月而直接走向成熟。至少对科幻文学来说,一塊砖一块砖地垒一堵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即使有梯子也没地方架。
我后来意识到科幻小说有许多种,也明白科幻小说中可以没有科学,也可以把投向太空和未来的目光转向尘世和现实,甚至只投向自己的内心。每一种科幻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能出现经典之作。
但与此同时,那3句对话所构成的核心理念在我心中仍坚如磐石,我依然认为那是科幻文学存在的基础。
虽然走了近百年,中国科幻文学至今也是刚启程,但来日方长,时间足够你爱